首頁>人物·生活>集·言論集·言論
付 瓊:康乾盛世的閨閣吟唱
【著書者說】
作者:付 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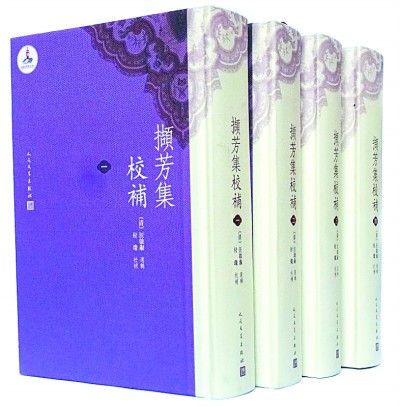
《擷芳集校補》(全4冊)付 瓊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女性詩歌,晚明以降,蔚為大觀,至清代康乾時期,達于極盛。汪啟淑所編《擷芳集》就是能夠反映這一盛況的詩歌總集。此書輯錄清初至乾隆末年約150年間女性詩歌6000余首,詩人1900余家,序跋、碑狀等生平材料40余萬字。筆者參校400余種文獻,完成了此書的校補工作。作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的最終成果,《擷芳集校補》(全4冊)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進一步加強了《擷芳集》以生平材料見長的特色,全面反映了康乾盛世閨閣吟唱的主要精神風貌。

清 陳枚 《月曼清游圖冊》圖片選自巫鴻著《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
1. 閨閣體與脂粉氣
清代有別集可考的女作家3900余人,是此前歷代總量的10倍還多。乾隆盛世女性詩歌的繁榮,不僅體現在作品數量上,還體現在更為本質的方面——“閨閣體”作為一種詩體的成熟。“脂粉氣”是它的標簽。康熙時期,唐孫華說:“夫閨閣之能詩者,間或有之,大都斗葉儷花,施朱和粉,短章小言,娟嫵媚而已。”(《凝翠樓集序》)顯然不滿于其脂粉氣。乾隆時期,女作家沈彩則說:“夫詩者,道性情也,性情者,依乎所居之位也。身既為綺羅香澤之人,乃欲脫綺羅香澤之習,是其辭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詩哉!”(《與汪映輝夫人論詩書》)認為身為綺羅香澤之人,就應該寫綺羅香澤之詩,否則就是脫離“所居之位”的矯情。二人對閨閣詩是否應有脂粉氣,可以說針鋒相對,基本代表了保守的男性作家與進步的女性作家之間的分歧。
今天看來,閨閣體之所以自成一品,正在于其“脂粉氣”,也就是源于女性立場、女性視角和女性氣質的顯而易見的女性特征。
“女性立場”是指站在女性利益上說話,從而使其作品獲得一種從男性立場難以發現的女性性別自信。在古代的中國,婦女的地位是以男性為坐標的,而王微玉卻說:“男兒封侯妾何有?要取黃金自懸肘!”(《詠木蘭》)莊燾則說:“楚王霸業已成空,留得花枝舞曉風。垓下歌殘紅淚濕,從來兒女即英雄。”(《虞美人》)此處“兒女”是“兒女子”的簡稱,專指女性。褒貶之間,男女有別,與王微玉詩的性別自信正復相同。又如徐德音《出塞》:“六奇枉說漢謀臣,此日和戎是婦人。能使邊庭無牧馬,蛾眉也合畫麒麟。”此詩貶抑“須眉”而揄揚“蛾眉”的傾向,也源于詩人的女性立場。這個立場以及由此而來的性別自信構成了脂粉氣背后的內在風力。
女性對某些物品往往有比男性更加敏銳的感受,形諸詠歌,也能自出新意,這就是“女性視角”。黃媛介《南湖竹枝詞》:“嘉興美女慣濃妝,絕樣南珠間翠珰。廣袖繡完裁四帛,外頭單罩紫綃裳。”陳麟瑞《閨詞》:“閨中喜作道家妝,云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廣東海澄縣的巧娘《春日冶游雜詩》:“載酒尋春上海航,銀盤先送吃檳榔。南人真是多情種,不惜纏頭脫鹔鹴。”姜素英《蘇臺竹枝詞》:“黃魚時節楝花飛,吳女廚中雪刃揮。分貯瓦盆贈同舍,郎從海口販鮮歸。”描繪豐衣足食的盛世景象,給人帶來風俗畫一般的新鮮感。又如王湘波《萍鄉道中》:“水村山店總離情,愁聽千林杜宇聲。賴有不殊鄉國處,兒啼犬吠與雞鳴。”“雞鳴犬吠”是鄉村和平生活的傳統意象,詩人在這里加上“兒啼”,就賦予了鄉村生活更有人情味的內涵,顯然得益于母親的視角。
閨閣體最本質的特征在于中國式的女性氣質,即偏于感性、略帶嫵媚又頗為矜莊的審美特質。清代女詩人多為畫家,其詩作往往“詩中有畫”,具有畫面般的感性沖擊力。黃汝蕙《楊柳詞》說:“幾日春光到柳條,臨流細學楚宮腰。西湖十里桃花路,又送鶯聲過六橋。”有色彩,有動靜,有空間,有層次,有轉接,寫出了早春西湖的生動景象。卞夢玨《湖樓》云:“一湖幽況送詩篇,畫閣初晴暮卷簾。兩岸煙嵐飛鶴點,數聲鐘磬醒鷗眠。山從虛鏡遺真影,塔向空天立自然。多少白云分片段,悠悠竟與遠峰連。”寫湖樓所見西湖晚晴時的景致變化,詩情畫意,渾然天成。再如江曇蕊《贈湘筠侄女》:“不倩新妝競畫圖,吟花昨夜醉流酥。黃鶯喚起嬌無力,半亸香肩小玉扶。”嫵媚動人。這樣的詩句出自男性之手,可能有些做作,出自女性之手就顯得自然貼合,妙不可言。
不過,女性詩歌中的嫵媚是有嚴格限度的。誠如吳年所言,“若乃身為女子,評花問柳,語茍涉乎微嫌,即噤口搖手,相戒而不敢出。”(《雪庭稿自序》)又如(美國)曼素恩所論,“至于女人的情欲,在盛清時期的中國,罕見直接的表述。”(《綴珍錄》)這一矜莊的特征是傳統文化打在閨閣詩上的深深烙印,使其嫵媚而不至于艷冶,從而與男性的同類詩歌區別開來。

清 陳枚 《月曼清游圖冊》圖片選自巫鴻著《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
2. 閨閣雄音
主流詩壇對閨閣體“脂粉氣”的譏評,迫使部分女詩人“故為剛厲之言”(何飛雄《望云閣詩集序》),以便獲得輿論的認同。也有女詩人,或者本來剛烈,或者學養富贍,識見超拔,心胸朗徹,與當時優秀士大夫相比,亦無愧色,發而為詩,自然英姿颯爽,與“故為剛厲之言”者有別。誠如清人所云,“閨詩多有帶英氣者”(《西皋外集》),這是乾隆盛世閨閣吟唱的又一突出特征。比如被其父王思任稱為“身有八男,不易一女”的王端淑,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頭”(《題藺相如傳》)之句,一時稱其豪拔。再如柳如是“輕財好俠,有烈丈夫風”(徐釚《本事詩》)。顧若璞與士大夫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其詩文多“經濟大篇”(王士禛《池北偶談》)。朱中楣“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與夫古今治亂興亡之故,仕宦升沉顯晦之數,未嘗不若燭照而數計”(李元鼎《隨草序》),“所為詩,規模韋、杜,雄渾方嚴,具有烈丈夫氣,概不徒以風韻取勝。每一篇出,藝林傳誦,稱曰遠山夫人,隱然香奩盛事云”(《西江詩話》)。顯然,這類“雄渾方嚴”的詩要比看起來充滿脂粉氣的詩更容易進入話題中心。毛奇齡女弟子徐昭華有一首《塞上曲》:“彍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近塞頻驅馬,尚有將軍夜獵還。”清剛勁拔,就格外引人注目,陳維崧謂其“閨中人作雄詞”,吳陳琰將其與“七絕圣手”王昌齡的邊塞詩相提并論。
閨閣而有雄音,俯拾即是,而且已經達到很高水平。胡秀溫《聽伯氏蒼頭話從軍故事》有“終朝罕見禾麥影,經歲不聞雀與蟬,塞馬黃羊遍地走,豺狼狐豕相摩肩”之類的描述,頗為雄肆。錢紉蕙《度梨關》:“迢遞逾梨嶺,肩輿勝兩驂。雄關限閩越,幽境極東南。地暖常多雨,云開忽作嵐。鄉閭望不極,聊復上塵龕。”筆力雄拔。乾隆時期,江蘇宿遷縣的倪瑞璇“博學通古今,凡經子百家、二十二史、《通鑒》《通考》,以及浮圖、老子之說,漢、唐、宋大家之文,皆熟復而融貫之”(瞿源洙《篋存詩稿序》)。創作“時藝約二百余首,古文約百五六十首,詩約千余首”(徐起泰《繼室倪孺人行略》),尤長于七律。其《閱明史馬士英傳》云:“王師問罪近江濆,宰相中書醉未聞。復社怨深謀汲汲,揚州表到血紛紛。金墉舊險崇朝棄,郿塢多藏一炬焚。賣國仍將身自賣,奸雄兩字惜稱君。”大意謂馬士英奸而不雄,一無是處。此詩斷制斬截,詞情淋漓,氣度沉雄,非同凡響。
清初女詩人兼畫家吳琪過著“嶺上白云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陳維崧《婦人集》)的生活,可見嫵媚與英氣本不相妨,其流風所被,遍及大江南北,康乾盛世的閨閣吟唱,正可作如是觀。如果撕下貼在閨閣體上的“脂粉氣”標簽,將閨閣吟唱的所有內容納入閨閣體中,則閨閣體并不排斥沉雄厚重之作。安徽歙縣的畢著(字韜文)“隨父宦游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尸為賊擄。眾議請兵復仇,韜文以謂‘請兵則曠日,賊且知備’,即于是夜率精銳劫賊營。賊正飲酒,兵至,駭甚,韜文手刃其渠,眾遂潰。追之,多自相踐蹈死。乃輿父尸而歸葬于金陵。”(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其《紀事》詩詳述此役云:“吾父矢報國,戰死于薊邱。父馬為賊乘,父尸為賊收。父仇不能報,有愧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瀌瀌,手握仇人頭。賊眾自相殺,尸橫滿坑溝。父體輿櫬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焉賦同仇。蛾賊一掃凈,國家固金甌。”當時只有二十歲。后來嫁給昆山王圣開,荊釵布裙,眉案相莊。其《村居》云:“席門閑傍水之涯,夫婿安貧不作家。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嘴種梅花。”其詩歌也由陽剛轉而變為陰柔。可見閨閣吟唱總體上偏于陰柔,其實不乏陽剛之作。有的甚至難分剛柔。如邵飛飛的父母貪圖錢財,將其賣為人妾,后為大婦所不容,竟轉配給家奴。其《薄命詞》云:“挑燈含淚迭云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柔中帶剛,正是在這個維度上體現了閨閣體的又一獨特性。

清 冷枚 《春閨倦書圖》 圖片選自巫鴻著《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
3. 時代自信
乾隆盛世的閨閣吟唱不僅有兒女情、英雄氣,還充盈著時代自信,它與性別自信一起,成為盛世吟唱的突出表征。黃嫆《漁者》云:“綠水青山春復秋,浮家漂泊卻無憂。花開古渡千杯酒,風滿寒灘五月裘。豈有渾流堪濯足,只應荊布慣蓬頭。圣朝況是寬漁稅,盡許偷閑狎鷺鷗。”“浮家漂泊”的漁民之所以沉浸在“千杯酒”“狎鷺鷗”的“無憂”生活享受中而沒有危機感,是因為相信“寬漁稅”的政策不會改變,其對于時代的自信不言而喻。
不過,盛世并不意味著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順境中的自信不難而易成,逆境中的自信難能而可貴。一個人身處逆境之中,仍然充滿對未來的希望,仍然堅守高尚的情操,這種自信才是有底氣的自信。這個底氣是個人才具,尤其是偉大時代,可以說來源于偉大時代的自信才是最廣泛最深刻的自信。乾隆時期,浙江秀水縣的徐錦嫁給塾師朱辰應,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生活十分窘迫。朱辰應說:“予嘗館于外,家惟一被,攜以去。至冬,妻擁敗絮,有覆無薦。每日之夕,伺兒女熟睡,即篝燈操作,漏三鼓,瓶火熸滅,兩齒相搏,矻矻有聲,則繞室環走,令暖氣自內出,即又操作如故。既解衣,兒女體若冰結,哺以乳,輒惡嘔,以故兒女都不能長養,而妻亦以此彌年疢疾縈其身。”(《亡妻行略》)但徐錦“高情朗韻,曾不因之少挫”,所作詩“風骨遒峻”(嚴蓉《紅余小草跋》),沒有半點可憐相。其《詠盆松》云:“自經剪拜別華峰,白鶴青鸞不復逢。屈抑貞心雖困守,正全高節避秦封。”又云:“欄下窗前聊自安,于今誰作棟梁看。任他挫折凌霄志,勁節依然傲歲寒。”在花盆的“屈抑”之中,從“華峰”移來的松樹已無法成為棟梁之材,但那種“傲歲寒”的品質并沒有因為環境的突然改變而改變。再如孫鳳臺《除夕》云:“病鬼貧魔擾一年,今宵甘分灶無煙。枯腸饑后如冰冷,瘦骨寒余似鐵堅。且爇爐香延永夕,何須杯酒斷愁緣。兒曹好學謀生計,只種心田與硯田。”大年三十,貧病交加,已經斷炊,也沒有酒可以澆愁。其實即使有酒,也無愁可澆,因為自己骨似“鐵堅”,能夠耐得這份饑寒。甚至正是得益于饑寒的磨礪,她的內心變得更加堅強,文章寫得更加精彩。她不僅沒有后悔自己的選擇,還要求她的“兒曹”像她一樣“只種心田與硯田”。又如安徽桐城盛氏,三十八歲嫁給江蘇溧陽孝子潘天成。潘天成“胸羅萬卷,囊乏一錢,氣欲凌云,家徒立壁”,販負以養其親,又師從當時著名科學家梅文鼎,學問大進。盛氏欽佩其德才,斂衽行師弟子禮,康熙三十年(1691)為其作勵志詩云:“君是江南一偉人,糟糠不棄得相親。志懷古道何妨傲,才過時流豈厭貧。補就寒衣腸寸結,借來村酒飲三巡。莫愁紙閣秋風冷,灰卻男兒四海心。”一對平凡的夫妻居然有如此強烈的自信,這份自信來源于個人的才具和品德,也來源于那個非凡的時代。
另一位“難女”劉蘭馨,早年“遭家變,攜老婢跋涉南北風塵間,卒能脫母于禍”,“以抑郁慘怛之忱,不得已而托之歌詠”,欲借此“破無知之口,發不平之氣,使一點靈臺,不致泯滅”(聶皓《黹余偶得序》)。其《贈義俠嵐峰邵人》云:“青天碧海恨茫茫,幽怨難教話短長。涉險履艱寧己事,披星戴月為誰忙?古心發處人如學,浩氣生時道合剛。自昔草茅多節俠,安能國史盡評章?”可以說于艱苦卓絕中錘煉出一副大關懷、大心胸,歌頌義俠不計艱險、救難扶危同時,何嘗不是歌頌自己小小年紀對整個家庭的擔當!我們同樣可以從這一份絕大的個人自信中看出源于時代的自信。
總之,康乾盛世的閨閣吟唱有脂粉氣,也有英雄氣,有小關懷,也有大關懷,有性別自信,也有時代自信,有高韻深情,也有精思妙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文學女性是中國文學的積極建構者,而不是無動于衷的袖手旁觀者和人云亦云的被動接受者。閨閣詩作為一種獨立詩體的成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表明,近現代中國女性文學的崛起是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特別是康乾盛世女性文學的邏輯延伸,而不是西方外來文化單方面影響的意外結果。現行中國文學史對古代女性文學成就的慣性漠視和對近現代女性文學崛起的外向溯因,有悖于文化自信的時代旋律,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
《光明日報》( 2020年05月16日 09版)
編輯:董雨吉
關鍵詞:閨閣 女性 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