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人物·生活>高端訪談高端訪談
陳思和:百年新文學 百年新發展
時間發展,進入新的世紀,甚至走得更遠。百年現代文學僅僅是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開幕式。又正因為它具有整體性、未來性、發展性等特點,所以現代文學史是不確定的,隨著生活的發展變化,會不斷出現新的作家、新的形式、新的文學,我們通過研究未來出現的新文學現象,對整個文學史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所以,現代文學史是一部沒有定論、也不可能定論的文學史。這也是我們在1988年提出“重寫文學史”的理由,文學史是需要不斷重寫、不斷創新、不斷加入新的內容的。這就是文學整體觀的基本內涵。
學術家園:上世紀90年代以來,您在文學史研究中先后提出“民間理論”“無名與共名”“先鋒與常態”“潛在寫作”等學術概念,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人認為:正因為有了像您這樣一批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們學科才有了建構本土話語體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礎。您在提出這一系列自成體系的話語建構時,正是學術界大量引進西方學術話語的時候,來自西方的新名詞、新概念一度在中國學術界狂轟濫炸,您這樣做有沒有糾偏的意思?
陳思和:這是兩回事。我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提出過一些有針對性的新概念新術語,也被有些青年學者所接受,但我從來沒有自覺意識這是在營造本土話語。像我們這一代從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對于西方新的學術理論、學術觀念包括一些新的概念術語都是懷著天然的敬意。我們是從一個相對閉塞、自以為是的文化環境里走出來的,當年在大學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國外理論著作,吸取西方先進理念、樹立新的人類理想的學習過程,現在想起來都是歷歷在目,令人激動。
我很少直接引用西方的理論術語來解釋中國現當代文學,那是因為我的研究都是有意識地從實踐出發,在文學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我提出的這些理論話語,包括一些文學史研究的方法,都是為了解決學術上的實際問題而建構的。這里當然也融匯了西方理論資源,只是我已經把它們消化了,成為自己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譬如對民間理論的提出,我討論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問題,但是民間理論是巴赫金提出來的,我覺得用來解讀賈平凹、莫言、余華的小說特別合適。我討論民間文本隱型結構是借鑒了西方原型批評的理論,并且舉一反三而形成的。其他如法國薩特、卡繆的存在主義理論、荒誕理論、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與集體無意識等理論,都是我一向心儀的,也都貫穿在我的文本分析中。我后來提出文學的惡魔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先鋒與常態,都是來自西方理論和文學傳統。我有很長時間學習比較文學,學習西方文學理論,只是我不喜歡炫耀,更不會一知半解就拿來套用中國文學。我經常告訴學生,不要把中國文學僅僅當作證明外國理論普遍價值的一個注腳,但不等于我們一定要拒絕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拜倒在老子孔子話語的腳下。
賡續文化脈絡展示文化自信
學術家園:百年新文學是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如何體現著文化自信,延續著中華文化的根脈?
陳思和: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百年,古人說,百年積德。也就是說,一百年了,可以積累一點經驗,百年不過三代人,三代人就可以有傳承有發展,傳統就隱隱約約地形成了。中國新文化應該是一個學科。我記得在很多年以前,有個朋友與我閑聊時說過這樣一個想法,我至今還很贊成:中國應該有一門學科,叫做現代學。現代學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它的內容是現代的,語言也是現代的,進而研究問題的思維方法也應該是現代的思維形態。新文學白話文就是一個標志。這是與古典學相對應的學科,討論研究的是現代文化的種種方面,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教育、現代文藝、現代語言等各個領域的問題,這也是指向未來發展的學科。現代學與古典學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但更應該起到主導的作用。我們研究學問都應該立足于現代,立足于實踐;古代傳統在今天現代社會建設中能夠產生積極意義的,才是我們需要繼承發揚的優秀傳統,如果沒有積極意義,那就是死的傳統。這是理解傳統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化傳統不僅可以被容納到舊文化傳統中去延續香火,開拓未來,而且古代文化傳統(舊傳統)是通過新文化傳統的檢驗、批判、重新解釋以后,才得以復活傳承,才會有新的生命力。這個關系不能被倒置,套用孔子的話說:未知生,焉知死?如果我們不知道現代文化發展的狀況,沒有現代的社會實踐,又如何會知道舊文化傳統中哪些是有生命力、哪些是早就枯朽了的?
再說文化自信的問題。我認為,文化自信主要是體現為我們要對國家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信心。至于我們與世界文化之間的關系,照我的理解,一是拿來主義,二是多元主義。拿來主義是魯迅提倡的,他大致說過這樣的意思:漢唐時代的漢民族文化吸收了大量西域元素,就是因為那個時代中國比較強大,文化比較多元。而到了元代清代,漢民族文化自身衰弱了,才會有意識地拒絕外來強勢文化,企圖用自我封閉來挽救瀕臨滅亡的所謂本土文化。真正的文化自信就要求我們理直氣壯地去面對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吸取應該吸取的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營養,拋棄已經過時的封建落后的文化。這樣我們才能夠平等地與別的國家民族進行對話。其次是多元主義,就是要相信,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人口那么多,中國文化存在于地球上,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太主張用“走向世界”這樣的口號,好像中國不屬于世界似的,還需要特別去“走”進去,求得人家的承認。但是各個國家民族不同文化之間需要平等的交流,不是需要求同存異,世界文化本來就應該大放異彩,而不是以前殖民主義時代所強調的先進文化消滅落后野蠻文化,殖民主義的文化侵略本身就是極其野蠻的。
學術家園:您剛才說到文集前三卷是文學評論,最早一篇是發表在1978年8月22日對《傷痕》的評論,最近的一篇是2017年4月20日對《芳華》的評論,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您一直堅持在文學評論領域有所開拓,最深的體會是什么?
陳思和:我學習寫文學評論的時間較早,開始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盧灣區圖書館寫書評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是在當時主流話語陰影下寫作的,這次編文集我沒有收錄這些文章。我選了進大學以后為支持《傷痕》而發表的評論文章作為我的學術生涯的起點。傷痕文學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也是“文革”后現實主義文學重新崛起的起點。今年是恢復高考四十周年,明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愿意把我的寫作道路與這兩個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
文學批評,某種意義上說,是主觀性很強的寫作活動。批評是有選擇的。從1980年代開始,我就一直關注幾個作家,幾乎貫穿了近四十年的評論。我不是一個來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夠解讀的評論家,只有與我的興趣或者某種隱秘的生命要素吻合的作品,才會激起我闡釋的興奮。我是借助批評訴說我自己內心的某種激情。我曾經把批評與創作比作一條道路兩邊的樹,相看兩不厭,一起慢慢生長,不離不棄。我的評論與作家創作的關系,基本上符合這樣一種關系。
學術家園:您能否對自己四十年的學術道路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陳思和:我的學術道路大致分為三個方向:第一,從巴金、胡風等傳記研究進入以魯迅為核心的新文學傳統研究,著眼于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的探索;第二,從新文學整體觀進入重寫文學史、民間理論、戰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等一系列文學史理論創新的探索,梳理我們的學術傳統和學科建設;第三,從當下文學的批評實踐出發,嘗試去參與和推動創作。總的來說,我很慚愧,我們這代人學習起步太晚,在還沒有充分知識準備的時候,就被時代過早地推到了社會上工作,雖然多了一點閱世經驗,但是能夠學到的知識太少,恢復高考后有幸在大學里補課學習,但畢竟離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學者所需要的學識準備,有很大的距離。四十年來,我一直是抱著學習的出發點來研究各種學問,這七卷文集也僅僅是我學習過程中寫下的一點心得體會,也可以看作是我四十年來的一份作業,今天交卷了。
編輯:位林惠
關鍵詞:文化 百年 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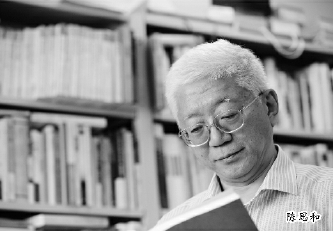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