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收藏·鑒寶>資訊資訊
歷史的文明 文明的歷史
? ——王震中委員談上古歷史研究與中國文明起源
編者按: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傳承文化、傳播文明需要民眾的廣泛參與,更需要深厚的理論支撐。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王震中,長期致力于中國文明起源、古代歷史的研究。本期學術邀請他來談談對中國文明歷史發展方面的思考與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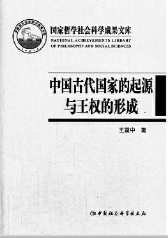
跨學科研究
探索重建中國上古史
學術家園:2015年,您出版了《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指出當代學者,在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具備長足發展的基礎上,有條件也有責任重建中國上古史。為什么要重建中國上古史?
王震中:為何“重建”?這是一個歷史問題。上世紀20年代以來,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疑古派(也稱“古史辨派”),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認為時代越晚,中國古史就被推得越早,古史人物就越詳細。比如在春秋初年古書中最早的神話人物是大禹,到春秋晚期上推至堯舜,到戰國中期則上推至黃帝,到漢代增加了“三皇”,再之后又加了盤古。同時,他們還對古書成書年代進行考證辨偽,比如推翻了《堯典》是堯時期成書的觀點,認為是戰國時期寫成,距離夏代很遠,不能將其當做夏代實錄。
疑古派是相較信古派而言的,相對傳統的疑古不疑經,這一學派對經書進行了懷疑,對古史人物譜系進行了顛覆。現在看來,有其“破”的一面,并掀起了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整理古籍的高潮。可是,一個時代的學問有一個時代的局限,現在學術界有些觀點認為疑古學派疑古過度,這暫且不論。我想說的是,上古歷史僅僅靠傳世文獻,“破”容易,“立”則困難,因為這些文獻材料多經遠古人們口耳相傳,雖保留了原始性材料,但又不免被各個時代加工,這就需要剝離加工的東西。怎樣判斷哪些是加工的,哪些不是?通過對史書的整理與考據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這就需要借助于考古發掘。于是,同時期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了“二重證據法”,提倡將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將出土甲骨文中所記載的商王對其祖先的祭祀譜系,與《史記》中《殷本紀》商王的世系一一對照,證明了《史記》中所記載的基本是正確的。王國維還把甲骨文中的王亥與《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天問》等傳世典籍中有關王亥的記載加以對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先生對當時的上古史研究范式進行了總結,首次概括為信古、疑古與釋古。這不無道理。信古就是認為古書上怎么寫,歷史就是怎樣的;疑古就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古書中屬于上古史內容是后人記錄的,不能完全相信;釋古則以王國維為代表。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受到疑古與釋古兩派的影響,更接近于釋古。后來隨著人類學的發展,二重證據法逐漸發展成三重證據法,即出土材料、傳世文獻與人類學材料相互印證。這就需要當代學者,既要對傳世文獻熟悉,又要對出土材料有所研究,還要深諳人類學,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重建中國上古史。如今,用三重證據法來重建中國上古史已愈來愈成為古史學界的共識。
學術家園:您提倡將歷史學與考古學、人類學相結合來研究中國上古歷史文化,這種跨學科研究,有哪些優勢與特色?
王震中:我多年從事國家與文明的起源研究,正好走的是將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路子。將三者相結合,我認為,既要掌握各自的優勢,也要清楚各自的局限。畢竟每一門學科,都有它獨到的地方,也有它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考古學通過遺物遺跡前后變化來反映社會歷史變化,尋求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是其優勢。但考古學需要學者利用技術、環境、人口學、經濟等知識對遺物遺跡作出符合上古時期的解釋與分析,則不可避免摻雜主觀因素,而且很多反映當時人類思想、制度、宗教以及社會生活的東西并不能通過考古直接挖掘出來。歷史學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上古史中的很多神話傳說,都是口耳相傳、后人追記的,流傳中存在逐漸失真的過程,古史傳說有“實”有“虛”,“虛”“實”混存,所以不能當做當時生活的實錄。關于人類學,比如國內外土著民族,即使在受到文明社會影響較小時,與幾千年前相比也是有變化的,因為社會環境在變化,自然環境在變化,自身也在變化。而對于每個民族來說,它的歷史是具體的,其他民族可起參照作用,但不能替代,這是它的局限性。
因此,國家與文明的起源研究,既是考古學實踐問題,亦是理論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需要二者緊密結合的問題。這需要我們跨學科整合三者優勢,彌補各自局限。這種整合,不可能是簡單的拼盤,而是一個以某一學科為主的有機整合,比如研究上古歷史,應以聚落考古學為主,去整合人類學理論,才能做出理論創新。
創新理論
闡釋文明起源與發展
學術家園:您致力于文明起源研究,其中文明與文化、國家總是緊密相連的,它們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王震中:研究文明起源,必然涉及“文明”的概念,又與“文化”糾纏在一起。相比文明,文化的內涵、外延要廣泛一些,文明則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比如文明社會,是相對之前的原始社會而言,文明社會是有文化的,之前的原始社會也是有文化的。
談到文明,還會涉及文明與國家的關系問題。我們把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社會到來的標志,但并非文明就等同于國家,兩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又有交叉和部分的重疊。歷史學家夏鼐認為,文明是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恩格斯說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由此可見,國家屬于社會意義上的文明,是文明的政治表現。從這一層面而言,文明與國家是重疊的,但文明包括的范圍更大一些。
學術家園:關于文明起源,您提出“中國文明起源途徑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邦國-王國-帝國”等學說,基于怎樣的理論基礎?與其他觀點相比,有哪些創新?
王震中: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國內外較為流行的觀點是用文明的三要素———文字、銅器和城市來探討文明的起源。我在1992年寫成、1994年出版的《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談到所謂“三要素”具有很大局限,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也難以對文明社會的出現作出結構特征性說明以及對其形成過程作出應有解釋。比如文字,南美洲印加文明雖已建立了強大的帝國式國家,卻沒有文字的使用;包括匈奴在內的許多游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會雖已建立了政權機構,卻也沒有文字。關于銅器,眾所周知,中國、西亞兩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是銅器時代,但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卻是沒有銅器的文明,西歐是在鐵器時代才進入文明社會的。城市也是如此,對于農業民族來說固然是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的中心,是其社會機構的物化形式之一,但對游牧民族而言則不是絕對性的東西,即使是農業民族中的古埃及也被稱為“沒有城市的文明”。
這就說明,文明的三要素,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因為,各古代文明所處的生態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其文明到來時的現象也不盡一致,這體現了各地文明社會演進格局的多樣性。考察文明起源時,應該將三要素看成走向文明社會的一些現象,而不是作為標準。因此我提出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文明的起源”,通過探討聚落形態演進階段的劃分來建立社會形態的演進模式階段,這樣就把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三者結合了起來。
通過聚落形態的演進分析,我認為,古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經歷了“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的演進路徑,歷史學家楊升楠稱之為“中國文明起源途徑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其中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包含了農業的起源和農業出現后農耕聚落的發展;中心聚落形態的不平等則表現為聚落內部出現貧富分化和貴族階層,聚落之間出現中心聚落與普通聚落相結合的格局;都邑國家形態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出現大批城邑,有的明顯屬于國家的都城。
這一理論對中國古代國家與文明起源的過程和路徑做了概括,那么,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古代國家形態和結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與演變?我通過研究提出“邦國-王國-帝國”說,認為夏代之前龍山時代的國家是單一制邦國,屬于早期國家;夏商周三代屬于多元一體的、以王國為“國上之國”的復合制國家體系,是發展了的國家;秦漢以后的國家屬于更加成熟了的國家,是一種郡縣制下中央集權的結構穩定的國家形態,是帝制的帝國體系。其中,秦漢以后的郡縣制與先秦時期的采邑、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世襲的,前者中的各級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針對這一觀點,有學者提出夏商周三代“邦國聯盟制”說,但依然無法解釋諸侯邦國要受夏商周王的調遣與支配,也解決不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問題。對此,我所提出的夏商周三代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制國家體系,得到諸多學者的認可。
歷史研究有多深
思想史研究就能走多遠
學術家園:您曾發表《建立中華思想史之當代中國學派》一文,基于怎樣的思考?
王震中:2014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主持編纂《中華思想通史》,請我擔任前三卷分卷主編。著書就要立說,以此為契機,我們提出要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之當代中國學派。中華思想史在人類思想史中,有很多獨特之處,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之當代中國學派,就是要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獨特道路的同時,做出理論的創新;在探討中國從古至今的思想特質及其演變的基礎上,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
當然,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之當代中國學派,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對中國歷史研究有多深,中華思想史的研究就能走多遠。中華思想史中各個階段的思想特質與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特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思想是歷史的精華。
學術家園:中國歷史或文明研究,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傳播以及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怎樣的理論基礎?在委員履職中,結合您所專長的研究領域,將有怎樣的關注與建言?
王震中:在國家與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幾年前,我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認為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最初屬于“自在民族”,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發展為“自覺民族”,當時人們用“華夏”“諸夏”“夏”“華”等來特意強調華夏族與其他族的區別以及華夏族的一體性時,不僅表明華夏民族已經形成,而且還表現出華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識上的自覺。很多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但我認為,到了秦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出現,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始處于形成中,比如秦漢郡縣里就包括很多少數民族。
在此基礎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學者,我認為目前在發展地方民族特色取得很大成就、更多強調民族參與性的同時,對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之上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強化得還不夠。怎樣強化呢?就是通過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在國家層面上,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增強國家認同的同時也就是在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因此我今年兩會的提案之一就是《關于加強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具有同一性的研究與宣傳》,既豐富了各民族的多樣性,又強調了各民族之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二者辯證統一。接下來我將關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入大學校園教材、相關學科設立發展的情況,最終還是想探索與研究這些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強化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具有怎樣的積極作用。
總之,在已經開始的五年履職中,我會發揮學術優勢,把平時研究、思考的問題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結合起來,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在推動自身學術發展的同時,更推動國家文化與學術的發展。
編輯:楊嵐
關鍵詞:王震中 上古歷史研究與中國文明起源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