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人物·生活>高端訪談高端訪談
期待崇尚科學的“第二春”
——單倍體骨髓移植“中國方案”的創造者黃曉軍訪談
2015年1月9日,2014年度國家科技獎在京揭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帶領團隊憑借“移植后白血病復發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體系建立及應用”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黃曉軍帶領學生在實驗室觀察單倍體骨髓移植數據。
白血病可以治愈嗎?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可能都要打上個大大的問號。
“白血病是不治之癥這個概念是錯誤的。”黃曉軍認為,通過合理治療,相當多的病人可以長期生存甚至治愈。
“骨髓移植是治療惡性血液疾病的有效方法。在骨髓移植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有供者。”黃曉軍介紹,在骨髓移植技術的早期,供者的主要來源是同胞兄弟姐妹,而且要求配型完全相合。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黃曉軍團隊找到了突破供體限制的新途徑,使半相合——也就是父母供給子女,或子女供給父母進行骨髓移植達到與同胞兄弟姐妹間移植同等效果,從而使骨髓移植的供體選擇從“有或沒有”變成了“選哪個更好”。
誰是黃曉軍?
相信絕大多數國人和媒體都不太熟悉。
對于黃曉軍,可以簡單用這樣幾段話來概括:
自西醫傳入中國至今,我國95%以上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來自于西方臨床技術。而他,恰恰就是那個95%之外——不到5%由中國人原創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的創造者之一;
他和他團隊原創的“單倍體骨髓移植體系”治療方案的出現,讓白血病是“不治之癥”的歷史終結。該方案還被世界骨髓移植最高學術機構冠以“中國方案”在各國推廣;
他還是迄今為止第一位站在美國骨髓移植會議(ASBMT)演講臺上的中國人。而他和他團隊原創的臨床醫療方案,成為目前全球一半以上治療白血病單倍體骨髓移植患者的首選方案;
因為突破了長期以來困擾世界的白血病骨髓移植“供體不足”的難題,他被西方骨髓移植界認為是中國的“下一個屠呦呦”,2016年底他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評為諾貝爾醫學獎的“明日之星”。
■期待科學“第二春”
3月7日,早晨7點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辦公室,剛剛結束查房的黃曉軍正在全神貫注地寫一封英文電子郵件。到了約定的時間,他準時地坐在了辦公室里。
利用黃曉軍起身迎接、倒水的時間,我迅速瀏覽了一下他的辦公室:不到6平方米的辦公室,除了一張辦公桌、一臺電腦、兩把椅子外,就是后面的兩個堆滿了各種書籍的大書架。
而我們的采訪就從本報今年兩會期間的特別策劃——《追問“陳凱先之問”》開始。
“我是5日看了你們3月3日那期《追問“陳凱先之問”》的。為了弄清問題,我又專門從網上搜索出去年兩會期間你們報道的那篇《陳凱先之問》。看了以后讓我沉思很久,內心的真實感受是沉重、興奮。說實話,有很多感觸。”盡管已經過去了幾天,當提起這個話題,黃曉軍依然一臉的激動。而他的同事和學生們說,黃曉軍盡管是一個性情中人,平時卻很沉穩,不是一個很愛激動的人。
“看了這兩篇文章之后,讓我一下子回想起中學時代。”黃曉軍說,那還是在他讀初中時一個春天的上午,學校突然組織全體師生在操場上學習一份文件。“這在當時不多見。后來才知道那是校長照著《人民日報》幾天前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所作的《科學的春天》的講話。除了照讀那個講話稿外,校長還向我們描述了當時中國的科技成就和百廢待興急盼科技人才的社會背景。”
雖然那時還小,但黃曉軍能感受得到那段時期和此后幾年里,全國上下都散發著崇尚科學的氣氛。而這種氣氛最初可能是在科技界內部,但后看來慢慢地擴散到整個社會——從高校到中小學,后來深入到了工廠和農村,科學走進了尋常百姓家。黃曉軍還依稀記得,“文革”后全社會掀起新一輪尊師重教之風,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形成的。而那時,無論是中學生還是小學生,你只要問他以后上大學學什么,在大家還分不清科學分類的情況下,很多人的回答多是“當科學家”。黃曉軍后來選擇學理科,就是受到那種氛圍的影響。
看到去年陳凱先院士與本報記者的對話和今年《追問“陳凱先之問”》系列報道,黃曉軍似乎覺得心里一下子輕松起來,“兩會關注這樣的話題,讓我覺得中國很可能迎來科學的第二個春天。”
黃曉軍也承認,說“科學的第二個春天”不一定確切。因為自1978年迎來“文革”后第一個“科學的春天”以來,中國在科技發展方面不斷前進,比如航天等很多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近30年來,中國一直都沐浴在科學的“春天”里。不過,黃曉軍也認為,從本世紀初開始,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更多關注對物質世界的追求。尤其是近些年來,一些人和媒體成了“傍大款”、“追星族”的追隨者和吹鼓手。甚至兩會期間也如此:一提起某某明星,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但說起當代中國的科學家,卻很少能說得出,甚至對中國科學領域取得成就的了解,遠不如知道哪些明星唱了哪些歌、演了哪些影視劇熟悉。“退一步說,你可以不知道科學家名字,但對科技取得的成就應該了解。”
黃曉軍補充說,不是說明星就不應受關注:“問題是一些媒體為博得收視率和眼球過分渲染和追星,留給本該著力宣傳的科學教育等的空間就很小了;而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助長了時下一些人尤其青少年瘋狂的‘追星’之風。這就讓這個年齡段的人本應該去探求的科學‘靠了邊’。我總覺得一些人和媒體的關注點出現了錯位。”而每當這個時候,黃曉軍總會有一種期待:希望中國能迎來全社會崇尚科學“第二個春天”,而這個“科學的春天”不只屬于科技者群體,而應該屬于全社會。只有全社會都崇尚科學,國家才可能真正走向富強。
■自信地發出“中國聲音”
2016年2月18日,“美國骨髓移植會議(ASBMT)”在夏威夷檀香山開幕。這是國際血液病研究領域中的頂級學術會議,在黃曉軍之前,還從來沒有中國人登上過這個會議的演講臺。這次,他應邀介紹了自己團隊的研究項目———“非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供者優化選擇體系”。這一移植方案,從2015年開始,被國際醫學界稱之為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也稱“中國方案”)。這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為數不多的中國原創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而一直以來,中國的西醫臨床治療方案被認為有95%以上來自于西方技術的拷貝。
作為一種惡性血液疾病,白血病的死亡率位居兒童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1位、成人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6位。按照傳統理論,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一致。但這種相合的幾率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1/2,兄弟姐妹之間只有1/4。而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只有十萬分之一。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多,供者來源就更加稀少。因此,骨髓供體來源不足成為長期以來困擾白血病治療的世界性難題。
要解決供者來源問題,最好方案就是單倍型,簡單說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況下進行移植。
早在1989年,黃曉軍也開始從事血液病臨床及實驗研究,接觸了大量病例。看著那些由于供者來源缺乏而走投無路的病人,他不得不逼著自己向前探索。
而彼時,世界各國也紛紛開展“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研究,這種方法只要求一半配型相合就可以,即“半相合”。黃曉軍解釋說,人類的遺傳基因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所以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染色體有一半相吻合。這就意味著,只要是有親緣關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堂表親之間,都有可能符合要求。如果這一研究取得進展,那么供者來源就不成問題了。因此他帶領團隊,從1996年開始進行探索。
遺憾的是,造血干細胞中有一種T細胞,不僅能抗腫瘤、抗感染,對正常細胞的殺傷力也同樣大。因而,采用“半相合”技術進行移植,常會出現令人頭疼的“抗宿主病”。由于接受移植的患者排異反應非常大,移植后生存率僅為20%。為應對這個問題,國外醫學界的研究,普遍著眼于將T細胞去除。但完全去掉T細胞后,患者術后出現感染和復發的幾率又有所升高,所以,“半相合”技術沒能得到推廣普及。
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黃曉軍調整思路,轉向中華傳統文化,期待從中“求解”。
“西方文化比較直接,不好的東西就要去掉。而東方文化則更加辯證和具有柔韌性。”黃曉軍認為,正如T細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不必完全扼殺它。他說,我國有一個成語叫“先抑后揚”,如果前期把T細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后期再把它發揮出來,這樣前期它既不會抵抗宿主,后期又能發揮抗感染作用。
自此,黃曉軍開啟了人體內抑制細胞排異功能的機制,并逐漸形成了中國原創的“單倍體相合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體系。
2000年,黃曉軍的第一例“不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病人,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康復出院。
黃曉軍很是欣喜,同時又很是謹慎,小心翼翼。“這就有希望了。接著我們做了第二例,也是復發的患者。”這一年,黃曉軍完成了5例單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并不代表你就成功了,因為一個好的臨床方案需要持續穩定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黃曉軍說。
2004年,當成功案例數達到100例時,黃曉軍在一個小型內部會議上通報了他的成果。
但黃曉軍的數據,并沒有如預料中那般得到同行的認同。他們在私下說:“你還真相信黃大夫那個結果嗎?我們都做了這么多,怎么就不行呢?”
受到質疑和挑戰的黃曉軍當時覺得自己很“冤”,但后來他慢慢體會到:“科學講究重復性,創新必然經歷非議。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完善,越多的質疑和挑戰,越能幫助你盡快成長。”
事實和數據能夠說明一切。黃曉軍團隊的成功案例數,隨著時間持續上升。
2007年,黃曉軍正式向北大醫院報告:造血干細胞移植供者來源難題已經破解,北大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體系”,從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復發等諸多環節有效解決了難題。
從2009年開始,黃曉軍應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邀請去作報告。在當時,MD安德森癌癥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干細胞移植中心,這里聚集著眾多該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
這里專家對黃曉軍的態度是:既有懷疑,但又覺好奇,想聽聽。他們私下的評論是:“中國人的結果你也信?”甚至一次會議上,一位美國專家“引經據典”表達他對結果的不信任,“恨不得就直接說你的東西作假”。
盡管英語不算“特別好”,黃曉軍卻并不畏懼。他認為,這就是中國人發出聲音的機會!除了爭取“說”的機會,他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堅持”。他堅信自己的方案可行,并不斷地完善它。
“其實,最早研究這一方案時,國際上已經放棄,團隊里也開始有人退出。他們說‘我們現在做了這么多,可是老外都不做了,我們是不是要放棄呀?’我說你這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意志,要相信紅旗一直能扛下去,怎么能自毀長城呢?不要以為外國人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他們一定有弱點,只是沒有給你發現。”黃曉軍從來不相信“國外的月亮比中國更圓”。
■為世界貢獻“中國方案”
執著追求讓他們的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如今,這種“人人有供體”的單倍體移植技術已經成熟,其術后成功率達到70%,與全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相當,而英美等國同類移植技術的成功率僅為40%。截至2015年底,通過該方案治愈的中國白血病患者已超過5000人。
目前,該方案在法國、意大利、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作為臨床常規應用,覆蓋全球50%以上的同類移植。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會正式命名為白血病治療的“北京方案”,并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并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協會相關指南引用。
“日本有20%的白血病患者找不到全相合的供體,采用‘中國方案’治療后,愈后效果良好。”世界細胞治療組織副主席下坂皓洋接受采訪時說,中國在白血病治療上的原創方案對世界影響深遠。歐洲血液學會前主席費比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方案”為白血病骨髓移植技術制定了新的標準,全球數千萬白血病患者都因此受益,“目前,歐洲、美國的患者采用中國治療方案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采訪結束時,黃曉軍指著電腦里還未完成的電子郵件說,美國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學會邀請他今年5月份去作年會報告,對方提出把他的《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來自中國的展望》演講題目改成《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的展望》。因為該組委會經過認真討論,認為他的這個報告不僅僅是來自中國的,更應該是世界的,理由是他的科研成果已經解決了困擾世界白血病骨髓移植有史以來的難題。而邀請他這位“跨界”科學家參加,在該學術年會史上還是頭一次。
“我現在最大的困惑是人才培養。”黃曉軍坦承,中國每年發生白血病的患者有20多萬人,需要骨髓移植治療的至少有8萬人,可現在全國一年只能做2600例半相合骨髓移植,其中北大人民醫院就占了800人。“原因一是國內還沒有重視,另一方面是人才匱乏。”黃曉軍說,他的單倍體骨髓移植方案早在幾年前就被世界骨髓最高學術機構向世界推廣,多個國家早已采用,但在國內卻沒有引起重視。直到這兩年,這一技術還是國內一些同行從國外引進來的。“他們不信中國人能弄出來,我們很多人缺乏自信。”此外,培養一個骨髓移植的醫生至少需要10年,現在很多年輕人一聽到10年就打“退堂鼓”,覺得還不如干點別的來錢快。說到底,還是因為不少人缺乏一種家國情懷,而社會也缺乏一種崇尚科學的氛圍。
黃曉軍說,科學家需要一種心系國家的情懷、甘于寂寞的精神,否則科學界本身就會出現浮躁之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很多科技發展與第二大經濟體還不匹配。科學發展才可能讓國家強盛,而科技發展需要很多人才,但更需要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氛圍。”
□相關鏈接
誰是黃曉軍?
黃曉軍,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國家萬人計劃、杰青、長江學者。長期致力于造血干細胞移植基礎和臨床研究,200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同年擔任“教育部創新團隊”學術帶頭人。其領導的研究團隊承擔包括“863”、“973”在內的20余項國家科研基金,建立了具有國際原創性的HLA不合白血病移植方案,在此基礎上領導建立并完善了國際領先的HLA不合移植體系;建立了國際原創的造血干細胞移植后白血病復發防治體系和移植物抗宿主病“預警預測-干預”體系。
他發展、完善了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體系——“北京方案”,治療白血病取得與同胞全合一致的療效,讓全世界共享“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時代。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會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并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相關指南引用。
黃曉軍及其團隊近兩年每年完成超過500例,累計超過3000例單倍體移植,成為全球最大的單倍體移植中心。
編輯:邢賀揚
關鍵詞:黃曉軍 單倍體骨髓移植 崇尚科學 中國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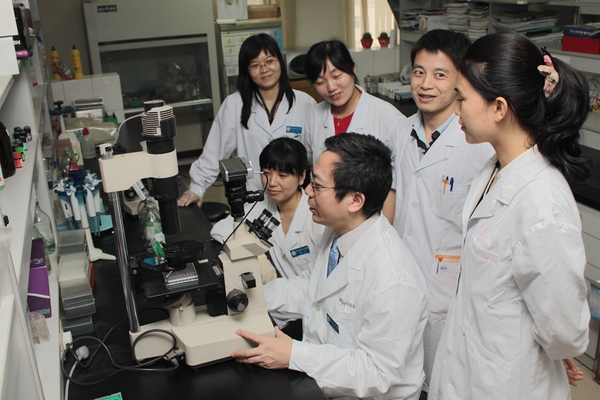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