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健康>資訊
浙大一院麻醉科主任方向明:與“無聲刺客”較量四十年
【人物名片】
方向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從事臨床麻醉、教學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尤其在膿毒癥致病機制和治療方面取得了系列創新性成果。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重點領域國際合作項目等15項,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項。

無影燈下,一場與“無聲刺客”的生死競速正在上演——靜脈麻醉后,方向明手持視頻喉鏡,將導管緩緩推入一位膿毒癥患者氣道,順利完成插管,隨后外科團隊開始手術。
這是方向明從醫近四十年來,與膿毒癥較量的又一次勝利。她已數不清接診過多少患者,在眾多急危重癥病例中,膿毒癥猶如“無聲刺客”,總是令她棘手。
方向明深知麻醉的重要性,這是患者手術時要闖的第一關。但她發現,傳統麻醉方式不太適用于膿毒癥,容易出現反流誤吸等情況,會直接影響后續手術順利進行。如何從麻醉角度尋找最優解,是她這些年一直在攻克的難題。
方向明的故事,知道的人不多。她和自己長期從事的麻醉專業一樣,在公眾視野中屬于“幕后”和“配角”。這些年,作為我國首位亞洲青年女科學家,且研究成果兩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等榮譽,才讓方向明被越來越多圈外人知曉。
自16歲考入原浙江醫科大學,除了畢業后有四年時間留學德國讀博,方向明的工作和科研軌跡幾乎沒有離開過浙大附屬醫院。
她深耕膿毒癥致病機制和治療,研發新型麻醉方案解決膿毒癥麻醉國際難題,惠及上萬患者;她推動多學科診療(MDT)模式革新,將臨床實踐智慧凝結為行業標桿。
不久前,我在浙大一院余杭院區麻醉科見到了方向明。溫婉的氣質,柔和而篤定的語調,在近一天的交談里,她分享著職業歷程與生活點滴,有喜悅,也有探索中的迷思。
方向明也會出其不意,偶爾轉換角色“采訪”我幾句,這份對人與事的天然探索欲,恰是她一次次攻堅克難、挽救生命的原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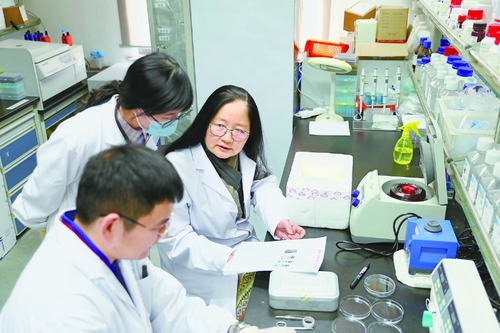
科學界的“撞墻派”
從醫近四十年,方向明對一些日常細節不太講究。比如那間我們兩人坐下來交談都略顯局促的辦公室,她說“夠用了”。可唯獨對一件事從不將就:攻克膿毒癥。
這是一種古老而兇險的疾病,時常發生在我們身邊——
一名五十多歲的大叔,因為手指劃傷沒去醫院就診,感染了膿毒癥;八個月大的寶寶,反復咳嗽一個多月不見好轉,送到醫院后發現竟然是膿毒癥;一場貌似普通的感冒發燒,也能進展成膿毒癥……
簡單說,膿毒癥就是人體在對抗感染時“用力過猛”,誤傷了自己,導致多個器官同時損傷,甚至衰竭。這個每年奪走全球上千萬人生命的“刺客”,病死率極高、治療費用高昂,發病原理至今還未完全闡明,國際醫學界一直高度重視卻踟躕多年。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即使在醫學技術領先的歐美發達國家,膿毒癥死亡率都接近50%。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出呼吁:“優先加強膿毒癥的預防、診斷和治療。”
當方向明決心研究膿毒癥時,朋友曾勸她慎重:涉及多學科,難度太大,且當時國內臨床數據幾乎為零。
“缺什么,就補什么。”方向明笑稱自己有些“叛逆”,偏愛走獨木橋,“我是科學界的‘撞墻派’,這堵‘南墻’,我撞定了。”
2005年起,方向明拉著科室里幾位同事,針對膿毒癥開展了國內首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先根據地域分布梳理出幾十家意向醫院名單。“剛開始對接時,經常吃閉門羹。”方向明回憶,有好幾次登門拜訪,大家圍繞相關研究領域聊得火熱,一提合作的事就說“再考慮考慮”,她知道這是被婉拒了。個中原因很簡單:這事太難,做起來太麻煩。
方向明沒泄氣,她改變了策略,翻開通訊錄,開始動用一切關系,找熟人幫忙牽線搭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于,北京、廣州、武漢等國內10家大學附屬醫院同意合作。
緊接著,團隊兩人一組,分頭奔赴各地醫院“蹲點”:有些醫院沒有電子數據庫,只能去資料室一頁頁翻記錄,找到病例后再電話回訪患者,了解詳細情況,不少患者還沒聽清來意就罵了聲“騙子”,便掛斷了電話;碰上醫院數據不全的,幾人就輪流值班等在ICU門口守候新病例。夜幕降臨時,大家一身疲憊回到住處,繼續在燈光下整理、分析、記錄。
2007年,凝聚了團隊無數心血的我國膿毒癥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終于發表,包括發病率、死亡率、感染病源等,填補了國內該領域的數據空白,為后續研究和醫療資源調配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地圖”。
向教科書“宣戰”
方向明性格溫和,但時常與困難“硬碰硬”。
“你以前愛看什么書,看過《十萬個為什么》嗎?”方向明突然問我,書中那些故事至今令她著迷,“我喜歡科學,喜歡研究。”
彼時,國內關于膿毒癥的相關數據庫有了,方向明還是找不到有效的治療方法。“現在回想,‘良方’其實就在臨床病例中。”
2007年的一天凌晨,還在睡夢中的方向明接到了急診室的電話。“有位腸梗阻患者病情嚴重惡化,需要立即手術!”
掛斷電話,方向明就打車往醫院趕。同一時間,患者的最新檢測報告顯示為膿毒癥。不料,麻藥推入病人體內沒幾分鐘,監護儀響起的異常“滴滴”聲,便打破了手術室的寧靜。“不好,患者出現了反流誤吸導致吸入性肺炎!”方向明心里一沉。
那天,從手術室到辦公室的路好像格外漫長,方向明回過神后,在筆記本記下了這個病例。短短幾行字,帶給她的沖擊卻很大:理論上,麻醉師要做什么她都知道,為什么這位患者還是會反流誤吸?
“從麻醉角度,是否還有更優的方案?”之后幾年,方向明在大量臨床病例和數據中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現在看其實不難,就是控制好兩個環節,呼吸和循環。”方向明打了個比方,麻醉過程好比飛機航行,起飛和降落階段是最關鍵的,專業上稱為麻醉誘導和復蘇階段。
呼吸和循環就處于這兩個階段,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得改變插管和用藥方案。
“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大家都做了幾十年,挑戰權威能行嗎?”方向明的想法一說出口,同事心里犯起了嘀咕。
首先是插管方式。方向明大膽提出,放棄常規的仰臥位,改用“側臥位可視化氣管插管技術”,舌根不壓迫氣道,自然就讓出了操作空間,同時也能降低因誤吸所致的窒息和嚴重肺損傷——就像睡覺打呼,側躺會緩解。
但翻轉90度,操作視線會被遮擋,對醫生技術要求更高。2012年,方向明帶著團隊花了整整兩個月反復論證、完善方案,終于通過了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核。緊接著,團隊利用磁共振開展側臥位氣道三維結構重建研究工作,為后續臨床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確保每個動作精準到位,方向明甚至專門請來中國美術學院的老師,讓她的學生當模特,把整個操作流程一步步畫成清晰易懂的示意圖。這五幅精心繪制的流程圖,至今還掛在麻醉科的走廊墻上,被大家戲稱為“方老師的武功秘籍”。
2015年,側臥位可視化氣管插管技術正式用于臨床治療。
在用藥方案上,她和團隊則創新性地提出了“滴定式麻醉誘導和復合麻醉方案”。核心就是“小劑量、慢慢加、個性化麻醉”加上“精準控制容量和速度”,像用滴管一樣精細調控,確保病人在麻醉過程中呼吸平穩、血壓穩定。
依托這些救治技術,團隊領銜制定了國際首個膿毒癥麻醉救治專家共識,被美國麻醉醫師協會采納和推薦,成為國際同行眼中的“中國方案”,業內專家贊譽這套方案推動了學科的發展。
2020年,相關研究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多一家醫院掌握這些技術,就能多救治一些患者。”如今,方向明的期望和努力,已化為一條實實在在的下降曲線——在示范應用醫院,我國膿毒癥死亡率從2007年的48.7%降低至目前的19.3%,核心技術在24個省、80多家醫院推廣使用。
不為論文為救命
就在不久前,方向明又用她的“側臥位插管”技術打了一場漂亮仗。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巨大的甲狀腺腫瘤把氣管壓得只剩一條細縫,最窄的地方只有2毫米,稍有差池,這條生命通道就會徹底關閉。
方向明果斷決策,在精準的鎮靜和表面麻醉下,采用側臥位技術,讓導管穩穩地穿過了那道“生死線”,順利完成手術。第二天,家屬發來了情真意切的感謝信。
已經不知道多少回,這種把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的興奮和成就感,總會讓她想起幾十年前那個普通的中午——
那天,母親跟往常一樣領著她去衛生院食堂打飯。“張醫生,來了個危重病人!”沒吃幾口,只見有人一路小跑沖進食堂,把母親喊走了。方向明習慣了這樣的場景,自顧自吃完飯,走回母親辦公室,坐在小板凳上看書。
兩個多小時后,手術室外傳來一陣嘈雜聲,緊接著是母親清脆的嗓音:“手術很順利。”方向明站起來,一蹦一跳往門外跑去。母親滿臉笑意,額頭的汗珠被燈光照得透亮,彎下腰捏了捏她的臉:“今天這個病人好險啊,總算是救回來了。”
年幼的她還不太懂那是什么疾病,但母親那一刻的笑容,像一顆種子,深深埋進了她的心里。
打記事起,方向明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衛生院。那時,母親是寧波一名“赤腳醫生”,工作忙沒時間做飯,天天帶著方向明上班。母親穿著白大褂給患者看病,她就在旁邊看著,有時還會模仿一些動作。
“現在我讀懂了那個笑容。”方向明若有所思,如今自己也跟母親一樣,無論什么時間,只要接到這樣的電話,就會條件反射地趕過去,從來就沒有想過“值不值”,而是本能覺得“就該這么做”。
或許正是醫者面對生命召喚時最本能的純粹,在和素不相識的人產生聯結的時候,“舍小家為大家”從來不是一句口號,是他們每天在病房、在手術室實實在在干的事。正如魯迅先生曾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和方向明息息相關的,在身邊,也在2000公里外。
2016年,在浙江省對口援疆項目的推動下,方向明帶領浙大醫療團隊來到新疆兵團第一師醫院進行幫扶。
第一次來到阿克蘇,一下飛機,湛藍的天空、廣袤的土地、成片的花朵,整個城市都在熱烈地迎接他們。而兵團第一師醫院的醫生,也早早在門口等候。
在醫院那幾天調研時,方向明看到病床上躺著幾位四五十歲的膿毒癥患者,很是揪心:“這些頂梁柱要是倒了,他們的家庭怎么辦?”幾天交流下來,她發現新疆醫生臨床處理水平并不差,醫療設備也挺先進,但膿毒癥死亡率就是居高不下。
“新疆太大了,病人送過來往往已經非常危重,留給醫生的時間和空間都太有限了。”方向明找到了癥結。她沒有簡單地傳授理論,而是精心挑選出自己多年積累的典型病例,用“仿真模擬”的方式,手把手教當地醫生實戰操作,努力提高成功率。
“醫學科研成果放在紙面只是冷冰冰的圖文,但應用到臨床中,拯救的卻是千萬人的性命。”方向明想的從來不是“我來救你們”,而是“要讓你們自己能救”。讓她特別高興的是,當地一支醫療團隊因為掌握了這些技術,后來成功獨立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千里之外的這片土地,總是讓方向明特別牽掛,也讓她更加珍視自己的價值。“退休后,我想常駐新疆,或者其他偏遠地區、農村。”
方向明心里裝著患者,也裝著一群“孩子”:她的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更喜歡叫方向明“方老媽”,因為大事小事,“方老媽”都會操心,有求必應。
采訪中,博士后葉慧還透露,“老師以前凌晨五六點到單位,看兩個小時書再上崗”。
“一個半小時。”方向明在一旁打斷。她總是通過一些具體的小事告訴學生要嚴謹,樣本是三個就是三個,要實事求是。
大多數時候,方向明又很包容,她希望給予學生足夠的成長空間,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做研究。目前,方向明已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157人。
而她自己,也喜歡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膿毒癥的難題至今還未完全被攻克,方向明又在“撞另一堵南墻”——細胞治療。如果研發成功,或可再次為世界膿毒癥患者帶來福音。
這就是方向明做科研最想要的回報,不為論文為救命。這并非英雄主義,而是一種對生命最樸素的敬畏,驅動著她四十年如一日,在寂靜的“幕后”,與那無聲的“刺客”持續較量下去。
編輯:馬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