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文化>評論
關于澳門:心淚汩汩的抗戰(zhàn)紀念文本
讀吳志良先生散文《孤島星光:抗戰(zhàn)(1941-1945)烽火中的慈悲之城 》相信用手中筆講述澳門抗戰(zhàn)故事的時候,全國政協(xié)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吳志良先生深情默默挑燈伏案,咸澀與酸楚一定模糊過他的視線。不然,為什么作為讀者的筆者,怎會感同身受地止不住淚落衫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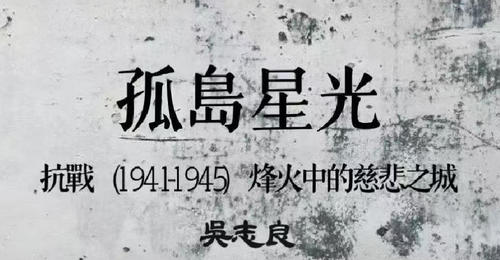
《孤島星光:抗戰(zhàn)
澳門,在吳志良先生的筆下,歲月鮮活。
只是,通過小人物的故事講述,多了難以數(shù)清的生動傳奇。
中山的疍民,嶺南大學的教授,上海青幫大佬的姨太,白眼塘街“義學收容所”的年輕陳姓女子、潮州阿嬤、上海小姐、風月場舞女、緬甸歸僑林叔、上海裁縫王太太、巷尾中山農民老陳、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兆麟和學生李秀蘭……
隨著怯弱
在吳先生的講述中,筆者從諸多的故事里,讀得四個字眼:殘暴——慈愛!
殘暴,是被樁樁件件的事舉側面佐證出來的。日本
小城澳門舉島展開的救濟、支援、互助、團結,共同繪就一幅人人自覺博愛慈心悲
于是,還原發(fā)生于澳門在地五年間的故事,每一頁發(fā)黃的記憶,都成為融入民族傷痛揮之不去的堅硬標識。
吳先生輕輕撥開歷史塵霧:澳門某女中學生、媽閣廟廟祝林德、瑪利亞方濟各修女,崗頂前的葡人別墅玫瑰園種蔬菜的主人,他們紛紛加入到大愛無悔的“義”的行列。當然,還有嶄露頭角的本地知名人士何賢、高可寧、柯麟、傅老榕……當然,還有澳門四界救災會的青年們鑄就的“海上生命線”、五桂山游擊隊、東江縱隊那出生入死的蓬蓬青蔥……這一切的一切,一再闡釋出這樣一條真理:中華民族不會亡!
先圣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各色人物的默默行為,無言大美,必得有一個中肯評述——幸已流瀉于吳先生的筆端。
吳先生的講述仍在繼續(xù),作品里,讓我們感動之處實在太多。
概率而言,文章以卷軸展開的書寫樣式,看似無有繩墨布置,卻盡顯自然高格,讓人感到壓心的沉重。五卷本的敘述,每一卷都似在探尋并豁開島城眾生人性善良的根底。渡海、共命、暗線、微光、星火,每一卷,都在高度凝練又生動傳神中獨立成篇又都用“慈愛”相系,歸于悲愴美!
綜觀全文,也讓人品味出韻律節(jié)奏之感。這韻律,已非池塘春草謝家春,而是真與善的契合,加上吳先生的才情,以及他一貫的志趣,致臻真正的美爆。想這也是來自他長期耕耘澳門,養(yǎng)成對澳門無與比肩的深摯情感,即大仁大愛從而倉中儲粟,豐滿實在,運用起來信手拈來的緣由。
而結尾終章,再次點題,澳門的慈悲大愛,并沒有隨時光流逝而散去,他們正在恒長延伸,從基因的譜系中,成為澄明暉光,悅耳琴音。于此,筆者終于明白吳先生串綴起來的小故事聚合為磅礴力量沖決日寇殘暴的苦心,終于明白抗戰(zhàn)最關鍵焦灼激烈時候,澳門人人參與抱薪添火焚毀日鬼狼子野心的作為。一人一個故事,共同撐持了澳門慈悲大愛的天空。
馮友蘭先生曾有言:“好的藝術作品,不但能使人覺其所寫之境而起一種與之相應之情,且離開其所寫,其本身亦即可使人覺有一種境而起一種與之相應之情。”讀吳先生作品,亦復如是!筆者還想,憐惜普通生命,才有以凄厲之筆,書寫出斷腸之句,才有字里行間,溫厚之氣撲面,雄偉、遒勁之色盈心。
閃回到文本開頭,那個木盆漂至澳門的孤嬰,早已成為中華民族骨血的象征。由此,我們致敬這部澳門抗戰(zhàn)彌足珍貴的文存。
(作者商成勇系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二級巡視員)
編輯:張準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