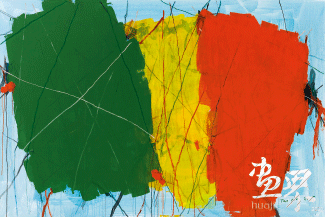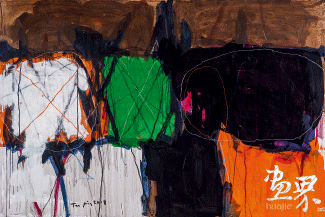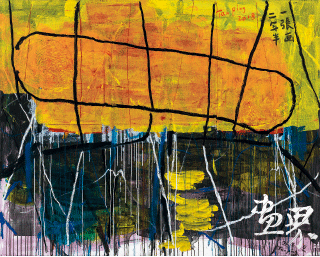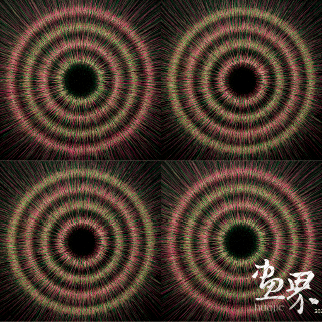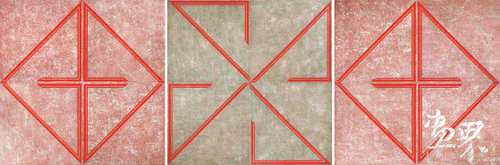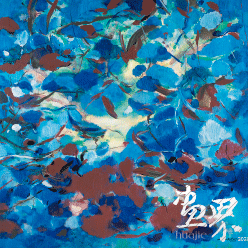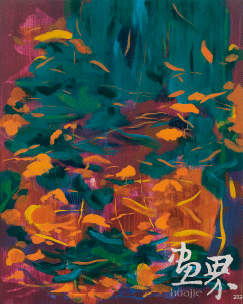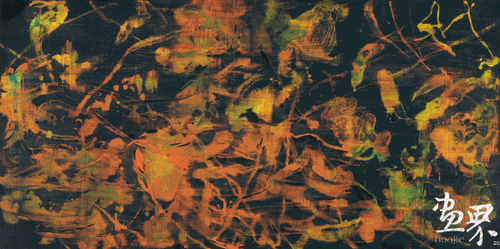首頁>書畫>畫界雜志>2020年第四期
秩序向—譚平、孟祿丁、顧黎明、陳思源的抽象藝術
“在藝術中須有一種秩序,也就是一種共同的東西,四位藝術家其實內在的文化氣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用抽象性的藝術語言方式,判斷和確定當下藝術訴求的多方位、多視角、多層次的藝術探索狀態(tài),借助共同的語言方式,試圖重新深化一種更趨自己的社會文化形態(tài)化的藝術探索方向。”— 顧黎明
再論譚平
易 英/文
譚平有非常優(yōu)秀的藝術感覺,也就是一個畫家在形式上的獨特感受性,別人感受不到的東西,他都能敏銳地感覺出來。上學的時候,我在壁畫系的走廊里看到他的水粉畫—靜物和人體,就覺得他畫得特別好,顏色和形式都有自己獨特的處理,不是那種油畫的調子,有點裝飾性,但是很寫實。那時我就想認識他,跟他學兩筆。
如果他沒有去德國留學的話,他會不會是一個表現(xiàn)主義畫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向完全的抽象?出國之前,他畫略帶表現(xiàn)性的都市題材。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他的都市題材表現(xiàn)就是很超前的了。他關注人和都市的關系,人在都市的處境,特別是精神的困境。他對題材不是特別感興趣,不會去深挖作品的主題,并且他透過形式琢磨出的抽象認識不是來自某種規(guī)則和價值,而是來自自身的體驗,任何再現(xiàn)的道理和抽象的原則,都不足以實現(xiàn)他那種無人能企及的感受性。
譚平的抽象首先是對現(xiàn)實與表現(xiàn)的跨越,這也是基于他的內在需求,他的超常的形式感召力。但他完成這個跨越之后,怎樣進一步發(fā)展就成了問題。對他來說,基本上有兩種選擇。一個是精神的介入,讓抽象的形式具有生命的意義。記號在譚平的抽象畫中有重要作用,或者作為構成的要素,或者作為精神的符號。譚平在這方面不是很明確,雖然達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一度把記號解釋為生命的某個階段的精神記錄,但是這有特定的時間規(guī)定性,一旦某個事件的精神影響在生活中淡化,這個記號將不再有精神的力量,甚至導致圖式的無意義重復。譚平最近的抽象素描就有這種可能性,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心境,產(chǎn)生特定的心理圖式,這一定要有外部的壓力,但我們不可能期待源源不斷的外部壓力。重要的是第二種選擇,繼續(xù)推進抽象的表現(xiàn),這是譚平藝術的本質所在。就他的作品來看,這是一個轉折點。從一個更大的范圍來看,這也是中國當代的藝術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架上繪畫而言,面臨著一種困境,一種突破。譚平在這方面,以個人的實踐為基礎,盡了很大的努力。
2000年以后,中國的當代藝術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多種可能性,尤其在材料語言、視覺形態(tài)上。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發(fā)展,以及大眾文化的泛濫和藝術市場的興起,架上藝術逐漸失去了以前的主流地位,抽象藝術也深受影響。抽象藝術是很難商業(yè)化的,抽象藝術的展覽難做,就在于贊助商不收抽象畫,不是他們不喜歡抽象,而是覺得沒有商業(yè)價值。市場的旁落可能更有利于藝術的思考和純粹,抽象藝術在當代藝術的角落里面更顯現(xiàn)出獨特的價值。前些年,正好有一個展覽,李向明和尚揚老師都參加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抽象上采用了一些材料,一些有限的現(xiàn)成品。這反映出抽象作為一種純粹的視覺表達,從傳統(tǒng)繪畫到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后現(xiàn)代社會、商業(yè)社會、消費社會所提供的視覺資源之間的轉換,從抽象表現(xiàn)轉換到極少主義的時候不會轉回到繪畫本身,而是轉換到裝置、影像。實際上整個繪畫開始出現(xiàn)邊緣化的傾向,盡管市場很熱鬧。這樣抽象就更加邊緣化,因為和它的前兩個階段—比如說后古典階段和工業(yè)化階段—那樣豐富的資源相比,它的資源非常有限,因為后現(xiàn)代的資源大部分是被直接使用的新的材料所取代,那么抽象藝術,我們把它叫作后抽象,它的可能性是什么?這就是譚平要探索的,它已經(jīng)不可能在原來從繪畫發(fā)展過來的抽象,從傳統(tǒng)、從古典發(fā)展過來的抽象這條路上走了。因為它的資源已耗竭,得添加材料、現(xiàn)成品的材料。
譚平在這里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就是不管別人怎么看,繼續(xù)推進自己的抽象藝術,而且他在骨子里認為這個東西是最好的。他不會跟我爭辯:藝術要不要轉型?架上藝術有沒有前途?他仍然在推進自己的“感覺”抽象,探求能否把自己那種獨一無二的形式感受挖掘出來。但是,他還是改變了策略,使他的抽象有了全新的變化,但仍然在框架內。不能說他的方式是前無古人,但還是有他的原創(chuàng)性,可以將他的新搞法放在“過程藝術”里面,過程并不是目的,過程實現(xiàn)的還是傳統(tǒng)的抽象,沒有綜合材料或平面裝置,有的是更深入的感覺挖掘。
可能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譚平的創(chuàng)作時間非常有限,很難有較長的時間對畫面進行經(jīng)營和思考。他的作品是分幾次完成的,每一次作業(yè)都是對前面的覆蓋,沒有小稿和草圖,也沒有既定的程序安排,在時間的緊迫中終止于偶然的效果,這個偶然效果可能也是潛意識中預設的方案。“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在無意識的行為過程中實現(xiàn)意想不到的效果。抽象表現(xiàn)主義畫家,如德·庫寧和羅斯科,都采用過覆蓋性作畫的方式,一遍一遍地涂抹顏色,或者是達到偶然的效果,或者是強調過程的意義。譚平的覆蓋有觀念的性質,但更重要的還是形式的創(chuàng)造,即抽象的表現(xiàn)或視覺的純粹。
覆蓋是一個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行為藝術的過程,也不是表演的要求,盡管他有些作品有表演的性質,如用視頻記錄他作畫的過程,圖像的不斷抹擦和重構確實有表演的成分。在這方面,他倒是有些接近波洛克的“潑灑”作畫,波洛克說形式有其自己的生命,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在行動的過程中,讓形式自動顯現(xiàn)出來。在波洛克那兒,形式顯現(xiàn)為最終的結果。譚平與此不同,每一個“過程”都是通向結果的一個階段,每一次覆蓋都是在探索一種新圖式的可能性,也是對極限的檢測。
譚平的抽象畫越來越大,大畫為覆蓋的可能性留有更大的空間。譚平說畫大畫是一種能力,因為小畫好控制,大畫難控制,創(chuàng)作大畫的每個過程都是面對一個局部,在處理這個局部的時候,要想到那個局部。在有形式的地方要想到?jīng)]形式的地方,這是一種無形的控制。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譚平的畫,不論是復雜的圖式還是極簡的單色,不管是痕跡、記號還是符號或構成,甚至那種把線條做到極致的搞法,都是多次復合的產(chǎn)物,是一個不斷破壞和重構的過程。
還要補充一點,最近看了譚平的新作,好像沒有那么多的覆蓋,主要是一次完成的抽象表現(xiàn),強烈的顏色對比,復雜與極簡的交錯,富于手感的線條,洋溢著樂觀的生命力。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覆蓋的結果,就像我們的長途旅行一樣,翻越大山之后,總會遇到一個盆地或平原,一片美麗富饒的景象,然后又會進入大山。
(文章有刪節(jié),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無-題(布面丙烯)120×120cm-2018年-譚平
無-題(布面丙烯)120×150cm-2014年-譚平
禁-行(布面丙烯)200×300cm-2015年-譚平
無-題(布面丙烯)200×300cm-2018年-譚平
一張畫兩年半(布面丙烯)160×200cm--譚平
不要被他隨性的外表迷惑—論孟祿丁
張曉凌/文
孟祿丁這個個案確實比較獨特,首先獨特在少年成名,他在大二的時候就畫了《在新時代—亞當夏娃的啟示》,這張畫影響很大,可以說是“新潮美術運動”的標志。當時大家都覺得很新鮮,因為中國人的視覺經(jīng)驗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中就是“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就是尊重焦點透視,在一個人的視野范圍內表達主題,你不能超越這個范圍。孟祿丁突然采用了一種超現(xiàn)實、超視覺的方法來表達沖破禁區(qū)這樣一個主題,一下子激起了美術界、乃至整個社會要求改革的人們的共鳴。孟祿丁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敏銳地捕捉到了改革開放年代人們的一種精神訴求,所以說他少年即成名。這件作品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我看現(xiàn)在很多人寫藝術史都要把這幅畫寫進去,就是說孟祿丁最初的創(chuàng)作就具有藝術史價值,這是了不得的。
第二個獨特的方面,就是“新潮美術運動”起來以后,本來是沿著語言本體推進的,結果跑著跑著就進入了功利主義階段,也就是說我們搞新潮美術的目的不是為了藝術,而是為了思想啟蒙,是為了給整個改革提供一種圖像背景。比如栗憲庭一直主張“重要的不是藝術”,這樣一來,政治就成為藝術的一個主要主題。如果政治是藝術的主題的話,那藝術又在哪里?我記得好像是在1986年后期,孟祿丁就開始質疑了,他從新潮美術的發(fā)動者變成了懷疑者:藝術難道永遠做政治的工具?做思想啟蒙的工具?他認為藝術不止于此,藝術有它自身的價值,即語言、形式、色彩,線條等有獨立于政治以外的超越性價值。所以他寫了《純化語言》的文章,開始反對當時的動向,要把藝術從政治的戰(zhàn)車上解脫出來。但在那樣一個大的形勢下,孟祿丁的聲音相對于整個“新潮美術”浪潮來說還是比較微弱的,不過這個聲音顯得非常清澈。
這兩件事就證明孟祿丁在二十幾歲的年紀就擔當起了新潮美術的推動者、懷疑者這樣的角色,有意思的是,這個角色的前后還是矛盾的。他在《在新時代—亞當夏娃的啟示》以后,類似的作品就很少了,緊接著轉向了抽象藝術,強調藝術的相對獨立性。緊接著他就出國了。當他去德國、美國轉了一圈回來以后,畫風有比較大的變化,對此各種解釋都有,我認為可能更多地指向了他的本心。就是說過去可能更多的是考慮一些社會問題和時代訴求,把繪畫弄得太復雜了。回國以后他用機器作畫,就是要把藝術純化,對物質、生命、藝術本體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即“物自體”包括顏料、畫布和機器之間構成了一套自在自為的生命體系,其運動的結果是你根本無法想象的。
你別看孟祿丁平時嘻嘻哈哈的,實際上他比較喜歡讀書。在同代人中,他是悟性絕佳的一個,這是上天賦予的。孟祿丁還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他這個人不動聲色地就轉換了自己的語言,他每次轉換都沒有什么特別明顯的標志,自然而然就轉換了,等你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轉得非常棒了。比如他的新作“朱砂”系列,我也是剛剛了解到。我跟孟祿丁說過,回歸母體是所有民族的成名藝術家的一個標準。每一個人,不管你如何千變萬化,你了解多少國家的語言、文化、藝術,最根本的,就是你的手、腳是不是緊緊地抱住你的母親的土地。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為了有一天要更好地回歸母體,在這里才能獲得真正的資源。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孟祿丁從出國到回歸,從“新潮美術運動”的奠基者到懷疑論者,再到本土現(xiàn)代文化的建構者,這幾個大的變化已經(jīng)奠定了他在藝術史上一個基本的地位。事實上,他在藝術史上的地位遠比現(xiàn)在很多賣得好的藝術家要高。
孟祿丁是個清醒者,他的內心是嚴肅的,他對藝術史、對文化的發(fā)展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不要被他隨性的外表迷惑,他內在的情懷是個真正有風骨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有啟蒙情結,有英雄情結,有救贖情結。不是只為個人利益,而是以天下為己任。
(作者系中國美協(xié)理論委員會副主任、美術評論家)
元-速(布面丙烯)200×200cm×4-2013年-孟祿丁
朱-砂(黃麻、礦物質顏料)145×12cm-2019年-孟祿丁
山水賦
顧黎明/文
我們人類經(jīng)歷了三種觀看方式,一是祭祀、宗教性的觀看,二是人的自我審視觀看(此在),三是圖像化的觀看。兩千多年前的漢代畫像石所繪的三種場景:一為地獄的煉獄,二為人世間的日常,三為升天后的另一個世界。天堂里的這個世界不是羅丹地獄之門頂端上的上帝,而是以自然動物朱雀、玄武和青龍、白虎的替化,使人性終極轉化為自然的化身。這是人對生命的終極期許,也是人對自然的歸屬。而在今天這個科技高速發(fā)展的信息時代,傳統(tǒng)的人與自然的秩序體系卻逐漸被淡忘,甚至是擯棄,人們對自然的靈性感知基本退化。這是人類的遺憾,也是人類的悲哀!
其實,至今為止,我們的觀看仍停滯在兩個界地,即自然凝練的秩序和圖像化的移植,前者是語言化的技術層面,后者是無深度的“他者”視域。我們很難再從自然的秩序中來框定自我知性。所以,如何在科技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的當下社會,構建另一個人與自然契合的心跡世界,以反觀我們所處的尷尬境地,是揭示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空間的重要因素。
觀看是一種態(tài)度,觀看是一種反思。
其實,我們已不再生活在現(xiàn)代主義的英雄主義時代,個人自我救贖的語言方式很難表達科技信息時代的變遷,我們的觀看受制于圖像信息化的誘惑,虛擬的現(xiàn)實性左右我們的生存空間,乃至價值判斷,導致我們很難辨析這個被虛擬包圍的現(xiàn)代世界的真假。同樣,我們也回不去古人那種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融的境地。由此,在我對自己的質疑過程中,唯有呈現(xiàn)這種糾結的狀態(tài)印記才是真實的感受。這種印記應該是裹挾前人的歷史圖式,現(xiàn)實的沖突感受及圖像化時代所帶給我們的視覺單一甚至是蒼白。
雖然這個時代科學技術與消費文化無邊界地統(tǒng)領著發(fā)達的人類社會,總以為信息圖像化時代只是更利于自我發(fā)展的便利手段,所以,由圖像到圖像的歡娛互動成為一代代無窮無盡的游戲體驗。于是,觀看也在脫離以自然為參照的審視和凝視,在游戲化、戲謔性的虛構的“真實”中坦然呈現(xiàn)。
觀看的本質是面對真實凝練自我,而圖像信息化的真實卻是借助他人的眼睛的“真實”。所以,我們當代人的真實是借助“他者”的呈現(xiàn),也就沒有了自然為本的心性的價值判斷。
我的《山水賦》系列不是對真山真水的觀看,也不是尋覓遠逝的山水境地,更不是體味視覺的饕餮,而是探索傳統(tǒng)的山水秩序在今天所遭遇的問題。試圖效仿前人的對山水掌控的藝術要素,借助多重的媒介材質,通過“觸感”的痕跡,表達我自己在當代語境下與前人對自然認識的差異與沖突,呈現(xiàn)當下人的心理狀態(tài)。“觸感”不僅是對陌生事物的身體性感覺,也是人在世界中的身體性存在的方式。我通過仿效與追憶,在前人的歷史文化狀態(tài)與現(xiàn)實的在場沖突中,試圖重構一個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人與自然相互沖突的當代山水境遇,引人反思。
科技化、信息化、經(jīng)濟一體化的社會,讓國與國、人與人連在了一起,給我們的生存帶來了太多的便利,但我們失去了對事物認知與把握的鮮活性,沒有了人對自然依存的秩序感。前人對山水的感悟,恰恰使我們反觀當下人性的缺失。實際上,世界發(fā)展到今天,不是誰離不開誰的問題,而是我們人類重新審視自己建立起來的這個現(xiàn)代化的世界秩序有多少與休戚相關的自然相宜共生。
當“COVID-19”疫情肆虐歐洲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呼吁的“例外”又一次讓我們深度感受到暫時彼此的隔離所潛伏的社會危機,而拆除這一道道不斷困繞我們的藩籬,唯有人在自然的境遇里反觀自己,才會讓“例外”消解在人與自然的秩序和諧之中。
借用2018年我為思源寫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為啟示吧:“不傲睨于萬物”但又是難以企及的久遠。在科技化的信息時代里,人類又能如何掌控、平衡未來的世界?是否我們今天還有資格去得到精神與天地相通的境地?(文章有刪節(jié))
枯山水-395×146cm-2003-2016年-顧黎明
山水賦之二十二(卡紙上色粉筆、水彩、鉛筆及蠟紙拼貼等)150×93cm-2015年-顧黎明
山水賦-鵲華秋色NO2(卡紙上色粉、丙烯水彩及拼貼等)156×107cm-2019年-顧黎明
山水賦NO21(卡紙上色粉、水彩、鉛筆及蠟紙拼貼等)75×46.5cm-2016年-顧黎明
陳思源的新繪畫:斑斕的余象
夏可君/文
當前中國藝術的創(chuàng)造力在于回到自身文化根源性的想象力才可能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與感知方式。何謂此根源性的想象力?這是中國人原初面對世界的詩性感受:面對世界的變化無常,以蒙蒙如煙然的流動形式來回應此無常變化,還能夠賦予此變化以詩性的韻律,既要達到即刻幻化,又要透明如鏡,激活自然之新的可塑性,并且具有詩意的余味,面對現(xiàn)代性的無根狀態(tài),生成出新的余象。
作為一個酷愛詩歌的畫家,陳思源這些年一直試圖通過此詩意的感受來重新打開繪畫,與一系列詩人的密切交往與對話,讓他不斷尋找著化解物象與顏料的方法,使之釋放出詩意的氛圍,讓自然的靈氛與靈暈再次來臨。他內在地認識到,只有重新激活中國文化特有的可塑性活力,這既是自然元素的可塑性,也是顏料質感的可塑性,以水性的元素性化解油性的粘滯,并且重建一種詩意的靈氛,才可能讓新繪畫發(fā)生。
當代繪畫有待于回到個體手感與時代生存經(jīng)驗,詩歌可以最好地經(jīng)驗到個體生存的現(xiàn)代性感受,這就是無根的漂浮感,離開了此虛無的拔根感受,如何可能有現(xiàn)代性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家之所以在繪畫語言上沒有原創(chuàng)的貢獻,就在于繪畫語言不是從生命感覺上生成出來,或者無法賦予此感受以詩意的根源性塑造。面對此無根狀態(tài),更為不確定的變化無常,如何以藝術語言來塑造之,并獲得新的形象與形式語言?陳思源與詩人們的交往,加強了這種現(xiàn)代性感受的自覺。
如何讓生存經(jīng)驗及其表達的困難在繪畫上重新生成?陳思源在畫布上苦苦掙扎,直到撕碎各種已有的目光,在混雜而無序之中,讓色彩在幻化之中飄舞起來,在一個奇妙的瞬間,他似乎看到這些色片就是柳絮,世界最為基本的元素就是這些漂浮著的無根的柳絮,近天命之年的藝術家為何突然敏感于這秋日飄飛的柳絮呢?為何對無根飄散的柳絮狀物如此著迷?這是因為此絮狀之物觸發(fā)了一個嚴峻的時刻,一種悖論的經(jīng)驗:這既是秋日之成熟,一切已經(jīng)干透,還帶有果實的飽滿;但另一方面,此柳絮從枝條分離而在空中飛舞飄動,處于無根狀態(tài);一種現(xiàn)代性的生存詩意感受,也正是一種中年的詩意—果實累累又瑟瑟秋風,一種逆覺發(fā)生的時刻,絮意與絮感—這是秋天的詩意糧食,在詩意幻化的目光中獲得色彩與形式。
如何達到此詩意的幻化并在平面上打開透明的深度?陳思源就是一遍遍地畫,一遍遍再擦洗掉,反復擦掉留下的殘痕,使之具有多向性與不確定。而在空間層次上,彼此分離的柳絮或者色彩,在流動中建構不確定的物象,純粹從色彩的對比度與空間層次來建構畫面,并且通過顏料的化解,讓色彩透明,空間透明,并不陷入抽象的重復,而是讓漂浮的斑斕色彩,反復地交織與交錯,打開了內部的呼吸與透明空間,并且在畫面上營造出一種朦朧的詩意氛圍。
畫面本身在反復涂擦之后,還依然保留了一種薄透感,光感的透明度,似乎如同水彩,帶來煙嵐之氣,又有著薄膜的通透。這些絮狀物在漂浮著,又如同水墨罩染一般,畫家以水墨的呼吸性來化解顏料的粘滯感。畫家在營造畫面深度空間時,為了讓畫面透明的透氣感不被堵塞,經(jīng)常會停頓下來,觀察很久,幾乎不敢畫,即讓每一層筆觸都留下來了,又保持其模糊的過渡性,瞬間的觸發(fā)性,相互的呼應,每一片色彩,斑斕而熾烈,畫面在激烈的燃燒中,還保持層層的透明,一次次的重疊,又依然薄如蝶翼,打開平面上的虛厚感。
絢爛的色彩在畫面上隱含書寫性的線條,但一切處于化解與過渡之中,相互的召喚與呼應之中,色彩終于觸動了空氣與陽光,如同蝴蝶的翅膀在顫動中感應世界的細微變化,因此繪畫并不僅僅是色彩關系,而是讓色斑在不確定中相互尋找,這是飄浮中的相互吸引,這是萬物的隱秘合唱,這是世界的夢絮,是詩意的斑斕,是色彩的頌歌。
繪畫的色彩與筆觸通過悖論的關系而生成:破壞又重建,塑造又抹去。看似形成某種風景圖像,但在色彩的疊加中又被重新想象,自然的可塑性得以強化,局部看起來如同抽象,其實整體上隱含著無數(shù)可能的形象。因為反復繪畫之后,無數(shù)的筆觸都余留下來,讓畫面具有了新的生長因子,又因為擬自然之物,這就讓畫面生成為一種抽象化的余意,即讓每一道筆觸都僅僅具有剩余的意味,但在整體上,又生成出一種可能的形象,激發(fā)新的聯(lián)想。
陳思源的繪畫純然依靠色彩與筆觸的力量,不斷激發(fā)詩意的聯(lián)想,保持可塑的生長性,讓筆觸在反復涂抹之中,再次重新生成,如此的繪畫方法,就重新觸動了繪畫的平面,一種不斷抽象化卻又不斷接納自然的虛化,其詩意的余象,讓我們再次進入自然的密碼,傾聽自然隱秘的歌唱。
繪畫純然以色彩的細微差異與過渡,打開一個深度的迷宮式空間,這是充滿詩意色彩的迷宮,而且是詩意的深度,繪畫得以繼續(xù)。
美國抽象表現(xiàn)主義雖然讓繪畫回到了平面的平面性上,但喪失了自然性與詩性,而通布利試圖讓涂寫再次回到詩性與自然性,但還是過于表現(xiàn),對于自然的豐富性挖掘不夠。中國當代繪畫,就是更為豐富地重建此詩意性與自然性,帶有抽象的筆觸,但又并非抽象畫,而是一種余象的觸發(fā),是其色彩碎片的斑斕生長。
陳思源每日的繪畫,乃是與色彩一道生活,讓色彩具有詩意的靈氛,畫面上的色彩所打開的空間滋養(yǎng)了每日的辛勞,這是繪畫的獎賞。這是繪畫所具有的現(xiàn)代意義,它代替了詩意的貧乏,使之更為絢爛。尤其在一個影像復制時代,繪畫絢爛而迷人的色彩,可以讓我們重新回到生命的感性,面對日常虛無主義的侵襲,只有繪畫的詩意與內在的空間,讓我們可以抵御現(xiàn)實的傷害。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美術策展人、評論家)
回-聲19-2(油畫畫布)180×180cm-2019年-陳思源
延伸的秘語-No22-3(布面丙烯)150×120cm-2020年-陳思源
回-聲-No26-1(布面丙烯)150×120cm-2020年-陳思源
與物容19-3-80×160cm-2019年-陳思源
責任編輯:張月霞
編輯:畫界-邢志敏
關鍵詞:藝術 繪畫 譚平 孟祿丁 顧黎明 陳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