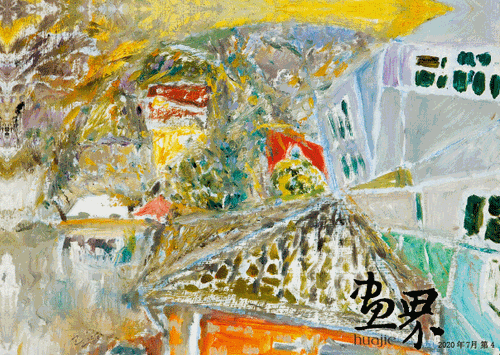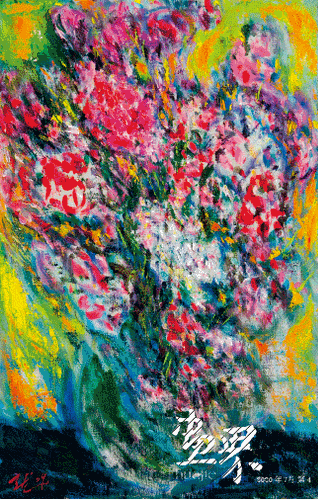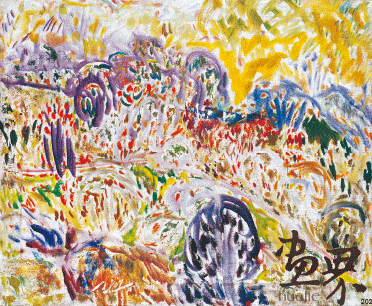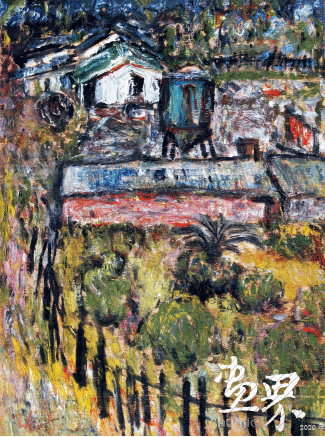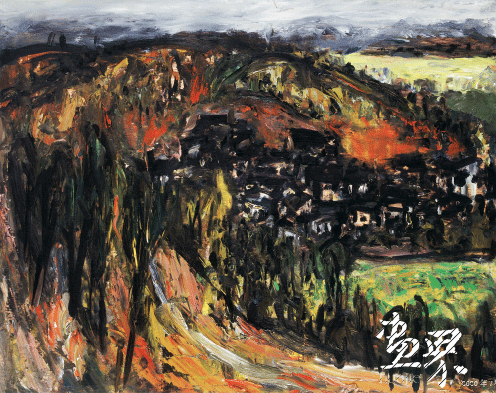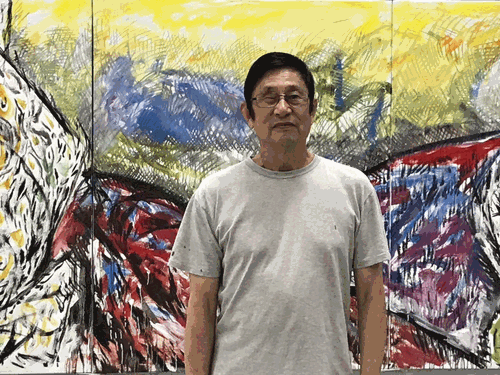首頁(yè)>書畫>畫界雜志>2020年第四期
放懷心象孤往者 天真爛漫老頑童
——我看陳天龍繪畫
沙塵天(紙面油畫)38.2×53cm-2010年-陳天龍
花之二(布面油畫)42×27cm-2009年-陳天龍
竹旁瓶花(布面油畫)53×65cm-1995年-陳天龍
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破帝制,歷民國(guó),建共和,歸途于改革開放,經(jīng)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美術(shù),作為民族文化的代表,播揚(yáng)著時(shí)代的音訊,傳誦著民心的吶喊。油畫這一源自西方的藝術(shù),在見證了歷史宏大變遷的同時(shí),通過民族救亡和文化啟蒙的磨礪,自我陶冶為東方新興文化的血肉身軀,譜寫出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與生態(tài)活化的生動(dòng)篇章。油畫在東方活化的漫長(zhǎng)進(jìn)程中,總有一些生動(dòng)的片斷,深入而直接地鐫刻了民族的精神臉譜,在當(dāng)時(shí)和后來,總讓人們不斷地由此追蹤某些意味深長(zhǎng)的文化變像。上世紀(jì)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中央美院舉辦的蘇聯(lián)專家馬克西莫夫講習(xí)班與六十年代初期在杭州浙江美院舉辦的羅馬尼亞專家博巴講習(xí)班,正是這樣的珍貴文化片斷。兩個(gè)講習(xí)班風(fēng)格迥異,她們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理念,甚至舉辦院校的先后分布,均成為文化史不斷考察、還原追探的命題。時(shí)至今日,作為那段歷史的當(dāng)事人,當(dāng)年的學(xué)員們的道路追求、歷史命運(yùn),仍受美術(shù)史界和教育界的格外關(guān)注和深化比較。他們的一生都與講習(xí)班無法脫離。“群必求同”,他們總是被作為某種符號(hào)、某類群體拋卻在二十世紀(jì)的美術(shù)天幕上。而事實(shí)上,他們的藝術(shù)追求也確然地受到這道印記根深蒂固的鐫刻,代表著這種文化西來變遷的歷史命運(yùn)的共像。無論人生多么坎坷,追求即歸蹤,命運(yùn)即家園。
陳天龍先生無疑是當(dāng)年浙美博巴講習(xí)班中用心最深、命運(yùn)最為多舛的一個(gè)。在其自傳中,陳天龍先生談到,他少時(shí)繪畫喜在綠葉叢中點(diǎn)上赭色,這其實(shí)就是一種挑戰(zhàn)與叛逆的青春隱喻。陳先生還深情回憶少年時(shí)看表哥在父親病榻前莊重而冷靜地作像。這種“向死而生”的藝術(shù)啟蒙,不是人人都可能遇到。僅此兩例,已然生動(dòng)預(yù)示了這位不斷被命運(yùn)推來搡去的藝者所必將領(lǐng)受的掙扎與命運(yùn)。進(jìn)美院就愛上俄羅斯十九世紀(jì)的詩(shī)性文化,后來又傾心法國(guó)十九世紀(jì)之后的繪畫,最后遇上了埃烏金·博巴,他明白了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兩個(gè)基本律理:一、“藝術(shù)應(yīng)顯現(xiàn)個(gè)性化的自由”;二、“吸取本民族文化養(yǎng)料以饗油畫,讓其有新的閃光點(diǎn)”(陳天龍《自述》)。縱觀陳先生談藝,總有一份放懷的頑童快意、高揚(yáng)藝術(shù)表現(xiàn)的爛漫,翔游在自由揮灑的世界中。他將畫者表現(xiàn)自我、不被物象束縛稱作:“有如雞雖是蛋中生,而雞非蛋。”他呼喊:“別把畫筆圈在籠子里打轉(zhuǎn)”,“無趣味的畫猶如一具本然美人。”這些畫家式的自白,狂狷而生動(dòng),姿肆而精彩,讓人感受到陳先生的脈動(dòng),他的不屈追求的心跳。那是非要到獨(dú)辟蹊徑、孤守困頓的深處才可能有的領(lǐng)悟。也是因?yàn)檫@種天性,使他能夠抵御命運(yùn)的種種打擊,置身山野,放懷界外,于孤獨(dú)中堅(jiān)守追求,于逆境中堅(jiān)守理想。這不僅使疾病低頭,而且也讓他在藝術(shù)和人生的困境中自尋其樂,以至在耄耋之年,藝術(shù)上還釀造出持續(xù)的飛躍和提升。
手捧陳先生的這本畫集(《陳天龍畫冊(cè)》),我心中頗感震驚。事實(shí)上,新千年伊始,我策劃舉辦“金秋放懷”畫展時(shí),與陳先生有過接觸。那是一個(gè)向一代師者致敬的展覽。但那之后,在新世紀(jì)的短短十年間,陳先生煥發(fā)新生,迎來了創(chuàng)造的豐碩金秋。這本畫冊(cè)半數(shù)以上的作品創(chuàng)作于這位藝者的耄耋之年,那些生機(jī)勃發(fā)、精神灑脫的無拘新作,均出自這位往昔師者的衰年變法,這讓人震撼不已。閱覽本畫集的前兩部分,第一部分受著歲月與蘇派的塑造,第二部分則是那個(gè)開放年代的生動(dòng)寫照。敏感求新的中國(guó)油畫人,幾乎將洞開的百年西方繪畫史過了一遍。以蘇派為主的造型基礎(chǔ)和巴黎的繪畫變革,這幾乎體現(xiàn)了上個(gè)世紀(jì)中國(guó)油畫人的兩個(gè)青春期,對(duì)于像陳先生這種年齡段的藝者來說,真正的尷尬是青春期后已臨老年。但陳先生的幸運(yùn)之處在于他所身處的美院的變革傳統(tǒng),在于博巴的教育思想對(duì)他潛入骨髓的影響,在于他心神深處的綠葉點(diǎn)赭的反叛與不拘。即便在前兩部分中,我們?nèi)钥梢钥吹街T般仿學(xué)之中深涵著的放手一搏的生命率性;看到的對(duì)自由、對(duì)民間、對(duì)自然弱小生命的樸質(zhì)關(guān)懷;看到受著山水詩(shī)性影響并蠢動(dòng)著的形式趣味。據(jù)說,在新世紀(jì)將至之際,陳先生遭遇車禍、大難不死,在零下6度作“黃山即景”,隱宿山岙“暮無山居”與大自然結(jié)伴作畫。于是本畫集揭開了第三部分,陳天龍先生仿佛又一次經(jīng)歷置身于死地之后的新生,雨過天晴,放手一搏。
在這里,我有一種揣測(cè)。中國(guó)美院是由一代大師林風(fēng)眠、吳大羽等創(chuàng)建。他們幾乎都是世紀(jì)同代人。新千年到來,美院舉辦了林風(fēng)眠、吳大羽系列學(xué)術(shù)研討與紀(jì)念活動(dòng)。這些活動(dòng)不僅拉近了陳先生與林、吳等一代先驅(qū)們同為淪落人與獨(dú)立者的精神聯(lián)系,而且先師們中國(guó)詩(shī)性情懷的歸宿,也重燃了陳先生心靈深處山水人生的詩(shī)性境界。陳先生完全打開,放懷在山居的孤獨(dú)無拘的生活中,放懷在擺脫具體寫景寫生、而將山水與心象一例相合相看的自由之中。陳先生仿佛一下子從對(duì)象化的風(fēng)景中跳脫出來,任憑天意,以心作畫。《聽鳥》的深碧既是林蔭又是歲月;《靜居水旁》聳立煙雨之中,無限孤單又無限堅(jiān)強(qiáng);《窗外街夜》將每日的夜觀變作夢(mèng)魘般的遠(yuǎn)眺;《稻熟》又將隔岸的觀望釀成心情的抒展與變奏。這批繪畫,學(xué)界稱之為中國(guó)意象繪畫,陳先生自己稱之為觸景生情的“心象”。“象”在中國(guó)文化中原本就是事物與心靈的中介,是將天人合而為一的整體。陳先生借茅屋草舍、離群索居,來歸皈自然懷抱,將往昔的執(zhí)著消解在山寂野處的灑脫之中,讓內(nèi)心與風(fēng)景融為一體。心因景而體象,景因心而含情。這個(gè)情是山水蒼然之情,這個(gè)象是天人的渾茫之象。如此濃重,又如此放拓;如此儼然,又如此豁然。天人相通,景心相渾。陳先生恍然進(jìn)入了一個(gè)恍兮惚兮的寥廓世界。
2011年.陳天龍先生畫了一組山水和《黃日懸空》,被視為中西合璧的經(jīng)典之作。當(dāng)我看到這山水中流注著肆意汪洋的濫觴之時(shí),我總是不由地想到中國(guó)千古山水詩(shī)人們,想到他們?cè)诘怯[傳統(tǒng)中的那些宏大視域。歐陽修的《中峰》:“一徑林杪出,千巖云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峰端。”多少人生的艱辛與逼仄,在此積成一份渾茫的意象,讓我們感受到那生命不衰、壯心不已的悲慨情懷。與此同時(shí),我還不禁想到林風(fēng)眠的蒼茫與吳大羽的疏淡。陳天龍先生仿佛閱盡艱辛之后,在自我救贖與抒情放懷的間隙,切近了先師們的觀照與知性的底蘊(yùn),真正地理解了唐人司空?qǐng)D《詩(shī)品》中所弘揚(yáng)的“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喻彼行健,是謂存雄。”于是我們讀到了如地火般燒紅了的丘壑;讀到了黑云翻墨、白雨跳珠的混茫;讀到了諧謔的排雨、豐膩的落霞;讀到了西風(fēng)動(dòng)草、落日暮云的勁健。《黃日懸空》,陳先生仿佛把我們帶到云端,“置身已在煙霞上,還有煙霞最上頭”(清·劉源祿《華樓》)。那真正的高天,只在行氣如虹的輕輕一抹,返虛而入渾,千古詩(shī)人的襟抱,正當(dāng)目前。
閱讀至此,我們跟著這位藝者的放逸之筆行走了很遠(yuǎn)。經(jīng)歷命運(yùn)的多舛,經(jīng)歷暮年的山居,經(jīng)歷登覽群巒的放懷,經(jīng)歷天真爛漫的頑童灑然,不斷地走進(jìn)了一個(gè)自由瀟灑的世界,走進(jìn)一個(gè)泰山秋水、向上超越的境界。這個(gè)境界,讓我想到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醉游洞庭寫下的:“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那敢將洞庭與月色相賒而醉殺洞庭湖的豪情,正來自陳天龍先生一生天真爛漫的頑童之心,以及數(shù)十年放懷心象的孤往之志。
(作者系中國(guó)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院長(zhǎng))
麗-山(布面油畫)50×60.5cm-2007年-陳天龍
院-落(板面油畫)61×45.5cm-2002年-陳天龍
山-村(板面油畫)48×60cm-2001年-陳天龍
風(fēng)(布面油畫)100×80cm-2009年-陳天龍
陳天龍近照
陳天龍,1935年生于浙江省溫州市,1960年畢業(yè)于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原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華東分院,現(xiàn)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1962年畢業(yè)于羅馬尼亞著名畫家埃烏金·博巴(Evgen Popa)教授油畫研究生班。1959年赴北京為中國(guó)革命軍事博物館繪制朱德油畫像及修改十大元帥像。
2006年,在上海美術(shù)館舉辦《守望自然—陳天龍油畫展》,在杭州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舉辦《守望自然—陳天龍油畫回顧展》,在北京中國(guó)美術(shù)館舉辦《心象空間—陳天龍油畫展》,2017年,溫州肯恩大學(xué)建立“陳天龍美術(shù)館”,授予肯恩大學(xué)榮譽(yù)教授。出版有《陳天龍油畫》《守望自然—陳天龍油畫作品選》《心象空間—陳天龍》《陳天龍》《一窗之見—陳天龍紙本繪畫》《陳天龍水墨作品》。
責(zé)任編輯:張?jiān)孪?/span>
文章來源:《畫界》2020年7月第4期“畫界人物”
編輯:畫界
關(guān)鍵詞:先生 天龍 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