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要聞>沸點 沸點
成都沉落千年古寺重現 證明市中心數千年未變
沉落千年古寺重現 這里仍是市中心
成都名寺福感寺此前僅見于文獻資料 今在實業街30號重見天日
“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
劉禹錫在《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中對這座寺廟非常稱道。
“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盡管此次只發掘了一部分,但已經可以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結合這塊經版上的寺名和盤龍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們基本確定了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人物‘章仇兼瓊’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
石刻造像栩栩如生、石刻經版上的金粉隱約可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昨日公布,歷經1年的考古發掘,位于市中心實業街30號的千年古寺福感寺日益清晰起來,此前其僅見于文獻資料之中。
福感寺從東晉延續到宋代,一直是益州名寺,在隋唐時期最為興盛,常有高僧駐留。唐代詩人劉禹錫贊其“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
實業街30號 暗藏成都千年名寺
2016年4月,實業街30號的考古工作開始推進,分開表層的鋼筋水泥,運走地下泥土沙石,一些造型各異的紅色砂巖、銘文銅瓦不斷被清理出來。眾多石刻中,一塊刻有“大唐益州福”的盤龍碑首引起了考古現場負責人張雪芬的注意。“這塊碑還有另外一部分。” 張雪芬解釋,根據碑后畫像可以判斷,石碑還有更多信息。帶有文字的石刻,就是通行古今的密碼。
后續的發掘中,“福感寺”、“章仇來臨”等文字紛至沓來,這讓考古人員將目光投向了一座在文獻中時有出現的名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易立介紹,福感寺的前身為大石寺,唐代成都干旱,地方行政長官到這里來求雨,每求必應。因此,這座寺廟改名為福感寺。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 唐末宋初,受幾次大的戰亂波及,福感寺逐漸衰落。
《妙法蓮華經》《金剛經》《佛說阿彌陀佛經》……1000多件石刻經版,筆力遒勁,不少文字上還隱約能夠看到一些金粉。上百件菩薩像、盤龍碑首、伎樂、天王以及裝飾構件陸續出土,足以完善南北朝到唐代的佛教藝術史。出土的菩薩造像,有的只剩頭部,但依舊面如滿月、安詳靜穆,一些殘存的造像則身披瓔珞,只剩一半的天王造像腳踏夜叉、氣勢威猛。
經版上的“章仇” 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
“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劉禹錫在《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中對這座寺廟非常稱道。“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盡管此次只發掘了一部分,但已經可以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概貌。”易立說。
“別看現在很多都殘破了,但還是能夠想象出它們的原形。”考古現場負責人張雪芬說,這些造像有的建于南北朝時期,高達三四米。其中一塊經版上刻有“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的字樣。
“結合這塊經版上的寺名和盤龍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們基本確定了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人物‘章仇兼瓊’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張雪芬說。
根據記載,章仇兼瓊復姓章仇,魯郡任城縣(今山東嘉祥縣)人,是唐玄宗時期的大臣。初任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長史、司馬。攻取吐蕃安戎城,累官至劍南道節度使。唐代高僧的傳記中曾提到,當年章仇兼瓊入蜀,途經劍門關時,碰上一位手持金雞的巨人,自稱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希望他挪一挪佛塔位置。因此,他來到福感寺將佛塔向東北移了42步。
福感寺遺址再次證明 成都市中心數千年未變
如果要大興寺院園林,經濟實力必須緊跟步伐。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佛教寺廟氣勢恢宏。福感寺周邊就有通錦橋的凈眾寺,不遠處的下同仁路還出土過140多尊以南朝時期為主的造像,一件單體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極為罕見的珍寶。據史料記載,兩晉南北朝到隋唐,600多年里,成都興建了大量寺院,現可考其名稱的就有43所。
還有先秦以來眾多遺存
除了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現了先秦墓葬80座,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隨葬品以陶器和青銅器為主,陶器器形較少,可辨釜、盆、罐、壺、尖底盞、器蓋等;銅器器形豐富,可辨鼎、鍪、敦、鉞、劍、刀、戈、矛、斤、鋸、帶鉤、印章等。對于探索這一階段的墓葬面貌和文化屬性、族群構成、先秦成都城的方位變遷、居址空間與葬地空間的關系等諸多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漢代的發現較豐富,除地層堆積外,還有甕棺葬、灰坑、房址、道路、水井、水溝等,其中道路、水溝的發現較為重要。 六朝遺存主要與市井生活關系密切,如道路、房址、水井、水溝等,以及大量的日用陶、瓷類器具和建筑構件。該區域地處秦漢以來的少城范圍,平時為郡縣一級的衙署公廨(成都縣治、蜀郡郡治)所在,一旦有警,又可作大城之屏障,且百工技巧,亦多在少城內,城外的西南郊除南市外,還有錦官城、車官城等小城,是名副其實的手工業生產和商賈互市的經濟中心。這部分考古材料,對于研究當時少城區域的城市格局和生活面貌有重要參考價值。
遺址年代一直延至明代
“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介紹,安史之亂后玄宗入蜀,成都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原址,從先秦到明代,一直都有人們生生不息的勞作,直到今天,這里依舊是鬧市繁華中心。
“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巍巍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王毅說。
成都商報記者 宦小淮
編輯:秦云
關鍵詞:成都 千年古寺重現 實業街30號 福感寺







 英國鳴禮炮慶賀小王子誕生
英國鳴禮炮慶賀小王子誕生 史上首位虛擬球童誕生 患病小球迷實現夢想
史上首位虛擬球童誕生 患病小球迷實現夢想 土耳其5.1級地震已致39人受傷
土耳其5.1級地震已致39人受傷 3名中國游客在埃及北部車禍中遇難
3名中國游客在埃及北部車禍中遇難 雅典市出任“2018年世界圖書之都”
雅典市出任“2018年世界圖書之都” 馬克龍展開訪美行程
馬克龍展開訪美行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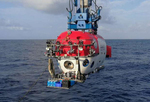 我國首次深海考古調查發現第一個文物標本
我國首次深海考古調查發現第一個文物標本 多倫多市政廣場降半旗悼念汽車撞人事件遇難者
多倫多市政廣場降半旗悼念汽車撞人事件遇難者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