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專題>2017全國兩會專題報道>策劃>追問陳凱先之問 追問陳凱先之問
羅永章:偉大的偶像喚醒偉大的自己
科學狂人,這是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羅永章給很多人的印象。果真如此嗎?此前只和他有過一面之緣的記者心里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2月25日,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抗腫瘤蛋白質藥物國家工程實驗室的一間二三十平方米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正在工作的羅永章。他趕緊迎上來,和記者握手,親自給記者拿了一把椅子。
記者環顧房間四周,沙發、書柜、墻上的地圖、窗臺上家人的照片,和其他專家的辦公室沒什么差別。但他的辦公桌比較“刺眼”:桌面他經常寫字的地方,已經爆皮了,他伏案工作的功力得多大啊,衣服袖子能與桌面產生如此大的摩擦力?辦公桌右側放著一臺舊的普通電腦,屏幕大概只有19寸。
“您就用這設備研究國際前沿課題?”記者有些疑惑。
“我來清華16年了,一直沒換過。就像這臺電腦,除了查資料、收發郵件,我又不干別的,夠用!”羅永章回答說。
再看這位大教授本人,個子不高,留著板寸,瘦削的面龐,一身土灰色的看不出新舊的休閑裝,腳上穿一雙布鞋,著實樸實。
“辛苦你跑一趟。這幾天有點累,嗓子不好,我們隨便聊聊。” 羅永章開始寒暄。
看了他的人,他的辦公環境,再聽了他客氣的山東口音,實在想不出他的狂。
但當談到自己的研究領域,他突然變了一個人,就像一頭精神抖擻的雄獅。
“科學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說話”
1987年,羅永章從蘭州大學化學系物理化學專業畢業后,赴美留學。那個年代,出國留學的絕對是少數,而出生于山東棲霞縣(現改為棲霞市)一個貧困小山村的羅永章能夠走出國門,并先后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求學,更是鳳毛麟角了。
記者開玩笑說:“山東棲霞有兩個名牌,一個是蘋果,一個是羅永章。”
羅永章笑著說,“沒有沒有,我不出名,我也不關心出名這個事兒。”
但是記者從圈里朋友了解到,在2014年青島召開的一次3000多人參加的生物醫藥領域的會議上,有了解羅永章的醫藥專家說了這樣一句話:“羅教授,如果說您在國內這個領域是老二,老大是誰呢?”
羅永章沒有回應,只是說,“科學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說話,而不是靠論文堆砌。”
在國內生命科學領域,羅永章可能還真的算不上出名。因為他很少參加國內的學術會,“很多會不能啟迪智慧,是在浪費時間。” 他說。
羅永章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實驗室里,鉆研課題,手把手帶學生。
他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羅教授幾乎就是一臺永動機,回國18年了,他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6小時,沒休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幾乎沒有晚上10點前離開實驗室的時候。
今年春節是個例外,他給自己放了兩天假,原因是打賭賭輸了,必須陪女兒回老家看望奶奶,而不是讓老人家來北京過節。
在美國,羅永章經常是在和導師的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或者在不經意間腦洞大開后,拔腿跑向實驗室。你可以說這是科學家的執著、偏執,甚至是神經錯亂,但是偉大的發現或許就是那一剎那的直覺。
18年來,羅永章帶領的團隊在腫瘤微環境、新生血管信號轉導、蛋白質折疊及分子伴侶作用的分子機理等生命科學前沿領域不斷結出碩果,確立了他在國內外生命科學領域的地位,特別是國家一類抗腫瘤藥物恩度的成功研發,以及在世界上首次證明Hsp90α是全新的腫瘤標志物,更使他的名字在醫生和患者中傳開了。
來自中國的小個子羅永章,因為解決了美國人沒有解決的技術難題,研發出活性至少是美國同類產品兩倍以上的抗癌藥物,入了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美國兩院院士、餓死腫瘤療法理論的奠基人佛爾克曼的法眼。老先生將其推薦給了另一個舉世聞名的大咖,被稱為“DNA之父”的詹姆斯·沃森。
“我也不清楚這兩個大名人之間發生了什么,反正他們經常電話或面對面交流,而我成為了他們某一次的談話內容,這絕對是一種幸福!”說這話時,羅永章就像一個考試得了滿分的孩子,臉上遮不住驕傲的神情。
另一個足以讓羅永章享有盛譽的事兒和一個會議有關。
美國冷泉港有一個小小的會議中心叫班伯里,這里不定期的召開著名的閉門學術討論會,用以指導全球某個領域的發展方向。之所以著名,不是因為這個地兒,而是參會者的身份,要么是諾獎得主,要么是該領域世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大咖,而且一定是應邀參會,總人數不超過36人(因為空間有限,最多只能放下36個座位)。在1977至2002年的25年間,有不少于39位諾獎得主參會(有一次會議的8個報告人中竟然有6位諾獎得主),著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就是在這里醞釀誕生的。2008年的會議主題是“我們如何治愈大部分腫瘤”,這一年羅永章入圈了,成為了首位入圈的中國科學家。“能參加這個會本身就是一種榮譽,而且是世界級的!這才是真正的學術峰會!”
“不能做井底之蛙了,我們應該有點國際視野。不然,從科技創新上,我們怎么實現從跟跑到領跑?” 不知道羅永章這樣發人深省的反問算不算狂?
羅永章(右)和詹姆斯·沃森在DNA雙螺旋發現60周年紀念會上
“詹姆斯·沃森,我一生的偶像”
在羅永章辦公室墻上有一張他和一位滿頭白發的外國老人的合影,他的 PPT里也多次插入了這個老人的照片。
“認識他嗎?”羅永章問。
記者仔細端詳,實在不知其為何方神圣。
“他就是剛才我提到的詹姆斯·沃森,DNA雙螺旋結構發現者之一、諾貝爾獎得主,我一生的偶像!”羅永章使勁兒在紙上寫下他的名字,說話的聲音也異常堅定。
記者只是輕微地點了點頭,似乎想起了n年前中學生物課本上見到過這個名字。
見到記者反應平淡,羅永章提高了嗓音,進行了十分認真的介紹——詹姆斯·沃森是和達爾文、愛因斯坦一樣齊名的人物,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科學發現之一,成為開辟現代生物學的里程碑。
在他眼里,詹姆斯·沃森是健在的諾獎得主里對世界影響最大的。“自從小時候在書上知道了詹姆斯·沃森后,我就想將來要做中國的‘詹姆斯·沃森’”。
詹姆斯·沃森對羅永章的影響深入骨髓。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發現了太多的機理和信號通路,也發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有多少能對腫瘤患者有所幫助?所以,能夠將腫瘤治愈或者控制,才是最有意義的。”
正是大師吹響的這個沖鋒號,讓生性好強的羅永章成了沖在第一線的戰士,這種動力至今未變。
2008年、2010年,詹姆斯·沃森兩度專程來清華大學訪問他的實驗室。
2013年,他帶領團隊在世界上首次證明Hsp90α是全新的腫瘤標志物,并由此開發出腫瘤早期檢測的試劑盒時,沃森博士得知后興奮不已,專程派人送來賀信,信中寫道:“你和你在清華的同事向攻克癌癥這一目標又前進了一大步。”
羅永章在講述中再次回味這兩件事帶給他的無上榮耀,記者被他的激動和欣喜感染著,好像自己身上也貼了金。
對于取得的成績,羅永章沒有否認自己的努力,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人生需要一個偉大的偶像,只有偉大的偶像才可能喚醒偉大的自己。”
羅永章說這話有足夠的依據,60后的他青少年時期正是人們對陳景潤、華羅庚等科學家頂禮膜拜的時代。以他為代表的莘莘學子正是在這種科學崇拜中寒窗苦讀、負芨求學,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科技界的翹楚。
孩子們還有當科學家的夢想嗎?
“現在的孩子們還想當科學家嗎?年輕人還有這樣的偶像嗎?” 羅永章情不自禁地問道。
2005年1月,號稱“布鞋院士”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遙感地理學家李小文去世,之后沒幾天,青年歌手姚貝娜因乳腺癌去世。李小文院士的去世消息在幾天后才見諸媒體,之后的報道冷冷清清。相反,姚貝娜去世的消息轟動了媒體圈,不少門戶網站推出了專題報道,網上流傳著各地歌迷悼念姚貝娜,甚至為其潸然淚下的照片。
羅永章是通過一個朋友才第一次聽說姚貝娜這個名字。對于媒體對李小文院士和姚貝娜大相徑庭的態度,羅永章有些扼腕。
羅永章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尷尬。每年全國兩會,每逢他碰巧和文藝界委員在一張桌上吃飯,都會有不少年輕記者跑過來和這些明星合影,還經常讓一旁的他幫他們拍照。
對于這樣的現象和經歷,他再次講了詹姆斯·沃森的例子。
詹姆斯·沃森來清華拜訪他的實驗室時,不管是清華的理科生還是文科生,甚至很多藝術學院及清華附中的學生都跑過來,里三層外三層地排隊想請他簽名合影。可這只是在清華,只是清華的一部分學生。在美國,詹姆斯·沃森家喻戶曉,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認識這位科學大佬。羅永章去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參加會議時,多次看到只要詹姆斯·沃森出場,不管是坐在自助餐桌旁,還是站在走廊看墻報、和人聊天,總有人悄悄湊到他身旁,“借他”拍張照片。而沃森老先生經過半個世紀的適應,早已習慣了被人當做拍攝的道具,可以完全不受打擾的做自己的事。小小的細節體現了社會對科學那種自然的、非功利的崇尚,還有科學大家的平易。
在美國,大多數科學家也不被媒體關注,絕大多數科學家老百姓并不認識,但科學家群體的社會影響力和公眾對他們的尊重都是無容置疑的,科學家雖然成不了富翁,但生活條件、待遇等各方面,也算很優厚的。
但在中國,這種氛圍還較差,至少崇尚科學、尊敬科學家的氛圍還不夠濃厚。相反追星、崇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風氣卻很盛。另一方面,我國個別科學家也開始偏離科學家應有的狀態,正走在自己“造星”的路上,高調在媒體上頻頻露面,跨界高談闊論,甚至誤導公眾,這最終將破壞科學家群體的公眾形象。
“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泥沙俱下,我們把西方好的壞的東西全引進來了,由于缺乏正向引導,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改變,很多人對金錢名利的追逐太強烈了,社會也變得浮躁。” 羅永章說道。
在這方面有些媒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媒體一味迎合受眾口味,對明星、官二代開什么車、住什么房、身價多少、一年收入多少等花邊新聞過于關注,這種情況不僅不利于社會正確價值導向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會害了孩子。
羅永章在自己女兒身上也受到了震動。
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地震,羅永章和女兒準備為災區百姓捐款。當時他想的是能捐多少捐多少。于是跟女兒開玩笑說:“爸爸把家里所有的錢都捐給災區好不好?”女兒當時正在吃飯,立馬用筷子指著羅永章說“不行,那是我的!”羅永章當時非常吃驚她這么點就知道有繼承權。他和女兒說 “寶貝,如果你不能自食其力,留給你的錢再多,你可能都會一事無成,最后會害了你。等你長大后我再給你解釋。”
現在羅永章的女兒快15歲了,再也不問爸爸身后的財產該不該屬于她了。因為她知道了得靠自己努力才可能獲得生存的能力。“可是更多的孩子如果每天耳濡目染這些東西,他們還會產生當科學家的夢想嗎?如果想都不想了,我們的科研后備軍將來會如何呢?”羅永章表情嚴肅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羅永章
27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還能記得幾位?
羅永章不想在媒體上出名,理由很簡單,他需要一個安靜的科研環境。
去年,習總書記在“科技三會”上明確指出:必須認識到,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相比,我國發展還面臨重大科技瓶頸,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科技基礎仍然薄弱,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創能力還有很大差距。
打破科研瓶頸,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員發揚“兩彈一星精神”,默默奉獻,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創造出更多具有影響力的科研成果。
不過,羅永章還說了后半句話:“科學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圍和崇尚科學的精神不能被冷落。”
媒體是輿論導向的引領者,被譽為社會公器,他們對科學家的報道,對其科研成果的關注,對于傳播科學精神,提高百姓科學素養,營造崇尚科學的氛圍至關重要。
“從2000年到2016年,我國有27位科學家榮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大家能記住幾位?趙忠賢院士在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前在我國超導領域默默耕耘50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媒體可曾追蹤過?屠呦呦研究員在獲得諾獎之前,有多少百姓聽說過她?” 羅永章的發問讓記者后背直發涼。
在羅永章看來,在對科學家的關注和科學精神的傳播上,媒體顯然冷淡了。科學家需要感受寂寞,但他們也是人,他們也需要存在感。
2005年,也就是羅永章回國后的第6年,新藥恩度的成功研發,讓不少晚期癌癥患者成功控制了病情,延長了生命。對于仿制藥占比超過95%的中國,這意味著什么?
國內外媒體和業內人士對于該藥的態度卻天壤之別。
惜字如金的美國《華爾街日報》在2005年12月22日頭版用3000多字的篇幅報道了這則新聞,英國《自然·生物技術》雜志、哈佛大學《新生血管前沿》和《夢》等期刊紛紛報道,英國《自然·醫學》雜志報道稱:“羅永章以一種更便宜、更有效的形式使該藥物(內皮抑素恩度)重獲新生。”
國內報道不僅寥寥,而且還有一些媒體和專家認為該藥是假藥,是在國外試驗不成才跑回國內進行研究的。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羅永章的心境。他用潤喉糖在桌子上反復排列推演,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告訴記者這種聲音的荒謬。最后,他不得不搖搖頭嘆息道:“國內這種對待科技創新的態度讓我有些困惑。”“特別是一些學者的心態,我真的很難理解。在我心里,學者該做的事是不斷拿成果說話,而不是當評論家指指點點,或者變身職業打假或者醫鬧之流。”
但是,羅永章從未言放棄。相反,他在生命科學領域前進的步伐越來越堅實,因為國家扶持科技創新的政策越來越好,整體氛圍也在向好。
羅永章有個愿望,他說自己如果找到延長人類壽命的“鑰匙”,他希望讓詹姆斯·沃森再多活50歲(雖然他已年界90),那樣他即使在耄耋之年也會有無窮的戰斗力。
“知道埃隆?馬斯克嗎?就是美國發明特斯拉的那個,《技術狂人》系列文章的主角。” 羅永章又在考驗記者。
中國科協黨委書記尚勇在看到羅永章正在做的課題后說:“你若實現了你的夢想,你就是中國的埃隆?馬斯克。”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人的名字,第二天我讓秘書買來這本書,看完最后一頁后,對著他的照片說:‘早晚有一天你得來找我!’”羅永章說。
還好,記者聽說過此人。同時,覺著羅永章的瘋狂一點不遜于埃隆?馬斯克。
臨別之際,羅永章的表情恢復了平靜,他迅速跑在記者前面開門,還堅持送到樓梯口。科學狂人的影子突然又沒了……
記者手記:
全新肝癌標志物Hsp90α“亮”在哪兒?
盡管羅永章通過圖文拼命給記者解釋蛋白質的復性和折疊現象,但依然是對牛彈琴。他在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就略過吧。在記者看來,介紹羅永章的科研成果不得不說全新肝癌標志物Hsp90α(熱休克蛋白90α)。
2016年10月19日,清華大學發布消息,羅永章團隊在世界上首次證明腫瘤標志物 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的檢測,試劑盒已被國家食藥監總局批準在臨床中使用。該科研成果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
事實上,早在2013年,羅永章團隊就已經發現Hsp90α可用于肺癌檢測,并就此研發了定量檢測試劑盒。不過,此次的研究成果則更具歷史和現實意義。
首先看背景。中國是肝炎大國,目前有近90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2000多萬慢性乙肝患者,還有近1000萬的丙肝患者。肝炎得不到規范化治療,會引發肝硬化和肝癌。因此,中國也是肝癌大國。據世衛組織統計,全球每年新發和死亡肝癌患者一半以上在中國。而肝癌被稱為“癌中之王”,到了晚期,再好的藥物和治療措施也束手無措。因此,早發現、早治療是王道。
基于這個背景,羅永章證明腫瘤標志物 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檢測,可謂功莫大焉。
那么這個Hsp90α“亮”在哪兒?據記者了解,目前國內臨床公認用于肝癌檢測的標志物是甲胎蛋白(AFP),但靈敏度僅有50%左右。羅永章團隊通過平行比對試驗發現,與AFP相比,使用Hsp90α檢測肝癌有三個“亮點”:一是靈敏度高達93%,高出AFP近一倍;二是診斷AFP陰性肝癌患者的準確率為94%,彌補了AFP的局限性;三是診斷早期肝癌的準確率為91%,有望實現肝癌的早發現、早治療。
按理說,這樣的先進科研成果應該迅速推廣使用,但問題就卡在這兒。羅永章對記者說,試劑盒價格由各省自定,目前全國只有山東、四川、寧夏、湖南、河北、安徽等9個省份獲得物價審批,開始辦理進醫院手續。“但是進入醫院很緩慢,平均進入一家醫院要蓋6~8個章,需要半年到一年時間!”
記者愕然。難怪羅永章說,回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大塊時間都用在了行政流程上。
執著的羅永章真累!(本網記者 李木元)
編輯:趙彥
關鍵詞:政協委員 羅永章 全新肝癌標志物 科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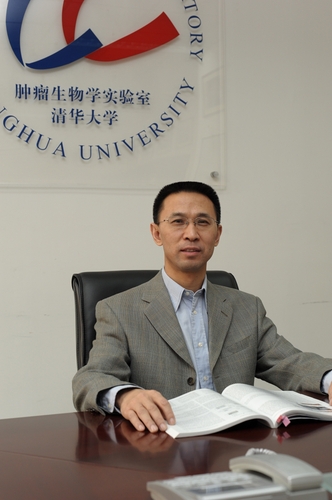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