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琴學大興,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濃厚興趣,“宋時置官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格古要論》)。宋徽宗本人乃操縵名手,對傳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專設“萬琴堂”珍藏“南北名琴絕品”,并手繪《聽琴圖》以名世,蔡京題詩曰:“吟徵調商灶下桐,松間疑有入松風。仰窺低審含情客,以聽無弦一弄中”。可見當時朝野上下,無不以能琴為榮,一部迎合最高統治者審美趣味的《洞天清錄》也便應時而生。
《洞天清錄》封面
唐代古琴大圣遺音(現藏故宮博物院)
聽阮圖 李 嵩 繪
聽阮圖 劉彥沖 繪
《洞天清錄》的作者趙希鵠,生平事履未詳。據明代張萱跋萬歷刊本《洞天清錄》,言其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端硯涌嚴泉,焦桐(古琴的代稱)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備用清福,孰有愈此者乎”(《洞天清錄·序》)。考慮到這樣高大上的人生情境并非常人所能想見,“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不拿出來曬一下簡直對不起觀眾,于是他便將多年來對各類古董珍玩的鑒賞心得與審美經驗公之于眾,“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錄》”,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條。與中國傳統琴學論著偏重于琴曲解題、琴人傳略、演奏技法、審美意趣不同,《洞天清錄》主要是對古琴材質、斫制方法、形制樣式進行品鑒的經驗總結,“其援引考證,類皆確鑿,固賞鑒家之指南也”(《四庫全書總目》)。
唐宋時期,古琴制作工藝取得長足進展,從朱長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質,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盡美》)不難看出,古琴選材與斫制(良質、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審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無怪趙希鵠感喟:“古材最難得,過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錄·取古材造琴》)。古人在斫琴的實踐中發現桐木紋理順直,性能穩定且不易變形,音色極佳,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正如趙希鵠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里,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線細密、條達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而梓木紋理堅實細密,可以讓琴音在槽腹內回旋,取得余音繞梁的共鳴效果,適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制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洞天清錄·擇琴底》)。對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純陽琴”,趙希鵠指出“古無此制,近世為之”,雖然音色古樸渾厚,但共鳴效果不佳,“必不能達遠”,非為佳構。
對于古琴面料的選材,趙希鵠將其分為梧桐、花桐(泡桐)、青櫻桐、刺桐,“四種之中,當用梧桐”,理由是“梧桐理疏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于花桐明矣”(《洞天清錄·桐木多等》)。梧桐和泡桐歷來都是古琴制作的常用材料,梧桐木質比泡桐密度大,紋理交錯,結構粗密,質地堅實,材質較輕,有更好的音響效果。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長的為佳,但因梧桐不適用于建筑與日常器物,采伐較少,好的琴材極為難得。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梧桐還象征著高潔美好的品格,如“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經·卷阿》)、“天資韶雅性,不愧知音識”(戴叔倫《梧桐》);或是忠貞不渝的愛情,如“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孔雀東南飛》)、“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孟郊《烈女操》),正是梧桐這種獨特的文化品質,才使其成為琴材的終極之選。
用陰陽理論解釋琴材的選擇,大約始于北宋《琴書》:“凡制琴,以桐木為陽,楸木為陰”,陰材、陽材分別指琴底和琴面。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長方向分為陰陽材,首見于《洞天清錄》:“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不面日者為陰”。為此,趙希鵠還提供了兩種驗證方法,一是以水試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撫琴以辨別音色。對于后者,趙希鵠還頗為自得,認為“古今琴士所未嘗言”(《洞天清錄·古琴陰陽材》)。將音樂聲學的實踐經驗納入陰陽體系加以闡釋,在當時并不鮮見,我們只要略一翻檢同時代的《夢溪筆談》之類的科技典籍便可見其端倪。由于日照條件等不同,桐木材質也會存在差異,在音色上存在細微差別,當然是可能的。但居然能隨著旦暮、陰晴等環境變化而發生條件反射,甚至“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未免聳人聽聞。
在制作工藝與藏品選擇上上,趙希鵠提出“制琴不當用俗工”“擇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則,對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當時推重的“概念琴”頗不以為意,“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主張“依法留心斫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對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為名行詐騙之實的收藏品市場而言,倒不失為一針見血的確論。
(作者單位:泰州學院音樂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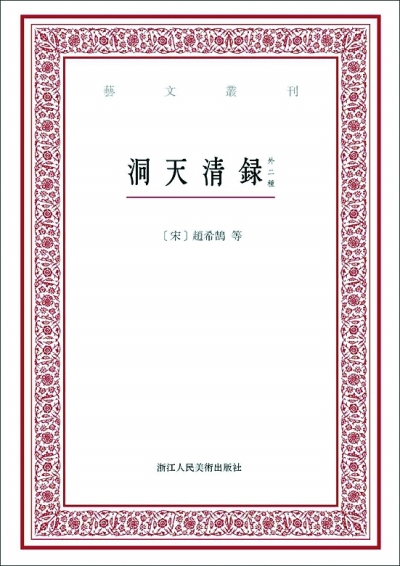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